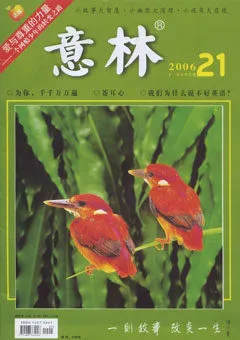我們為什么說不好英語?
凌 敏
我們從小就開始學英語,可十幾年后還是開不了口。我們考托福考GRE考雅思得了高分,可遇見外國人時,交流水平還是有限。但無論如何,別讓英語挫敗了我們的自信心。
“我沒有天分。”
有很多人相信“語言天分”這回事。是不是必須擁有特殊的才能才可以流利運用一門外語呢?答案是否定的。從20世紀20年代起,語言學家們就開始進行各種測試,希望證明這種才能的存在。1970年后,他們中的大部分承認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這一點。重要的是我們生活的環境、我們的個性以及主觀能動性。外向的性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幫助。對英語文化的興趣有益于英文的學習。當然你也可以踏上異國的土地,在那里待上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
“在我這個年齡,已經太晚了。”
錯!學外語沒有特定的年齡,當然,孩子總是比成年人要學得快。法國心理分析師布呂諾·阿爾古的解釋是:“一直到5歲以前,人的腦神經突觸都是打開的。所以,孩子能很快掌握一門語言,就像是海綿吸水一樣。在這個年齡以后,一個人不可能變成真正的雙語者。”在6~11歲,人們最容易掌握語音和詞匯。但理解力方面,成年人更有優勢。成年人已經學會了自己母語的結構,能更快地掌握外語的句法和詞法,也能更巧妙地運用記憶技巧,幫助自己學習。
“我對自己的語音感到羞恥。”
我們很多人都有這種體會,盡量少說或不說英語,因為我們不想說得怪腔怪調。中國的英語教育非常缺乏語音教學這一環節,而這導致了惡性循環:由于不能確定正確的發音,我們常常選擇不說;不說就缺乏訓練,對說英語更沒有把握;而碰上必須要說的場合,如果對方沒有聽懂,我們就更確認了自己的語音有問題;然后,我們就會說得更少。
法國耳鼻喉專家阿爾弗萊德·托馬蒂斯指出了導致錯誤語音的另一個原因:我們只能發出我們能聽到的聲音。因而改善語音,關鍵在于訓練聽力。他發現,同樣的聲音材料,德國人跟法國人聽到的就不一樣,而法國人跟中國人也大不相同。每種語言都有它的偏好頻率范圍。一個人越是習慣母語,越會過濾掉其他頻率,越難聽清楚其他語言。說外語,就是讓自己的耳朵與它的音波相適應。為此,他發明了“電子耳”來輔助人們學習外語。“電子耳”中收錄了廣泛的音頻材料,可以刺激耳朵擴大可以聽到的音頻范圍。
“我不想牙牙學語。”
嫌自己英文說得太幼稚,是很多人懶得開口的原因。操著一口流利母語的成年人,往往忍受不了自己過于簡單幼稚的外文表達。但凡事都有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語言學習尤其需要耐心和恒心。早期的簡單模仿是必要的。從這一步到相對自如地表達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想想多一門語言,就多一種思維方式,一段時間內的牙牙學語應該是可以忍受的。換個角度想,這正是和已經熟悉的世界拉開一點點距離。
“我怕別人笑我。”
“這種害怕往往可以追溯到兒童時期的某些焦慮。”布呂諾·阿爾古說。害怕自己不能達到父母的期望值,或者童年時期學業的失敗,都會在新的學習環境里造成阻礙。怎么辦?找出你焦慮的真正原因,明白障礙在哪里,并且在新的起點上重新開始。要想在別人的注視下取得進步,就要跟著一位老師上課。那究竟是跟班還是請私人教師呢?跟大家一起學習,會讓你有動力而且也能幫助你克服害怕的情緒。但是一對一授課更是一個讓你勇于開口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李陽的“瘋狂英語”雖然毀譽參半,但它確實可以克服別人注視所造成的心理壓力。
“我記憶力太差,一個單詞盯著看
了很久,寫了幾十遍也記不住。”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體會:像小學生學漢字一樣,把一個單詞在紙上寫個幾十遍。或者盯著一個單詞看半天,似乎英文也有偏旁部首。但最后它們還是不翼而飛,我們的腦子留不住它們,于是只有感嘆自己記憶力太差。
其實不然。研究成果表明:中國人大腦中的語言區與西方人不同!在進行文字閱讀時,使用表意象形文字的中國人的語言加工中心是左側額中回皮層,即布魯德曼分區的第9區;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的語言加工中心則是前腦布魯卡區和后腦的威爾尼克區。
布魯德曼第9區額中回皮層與運動區緊密相連,而威爾尼克區更靠近聽力區。所以,要想學好中文要多寫、多看、多說,靠“運動”來記憶;而學習英文應注重營造語音環境。專家認為,很多人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用學習中文的方法來學英文,所以,學了多年還是“啞巴英語”。
(曲川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