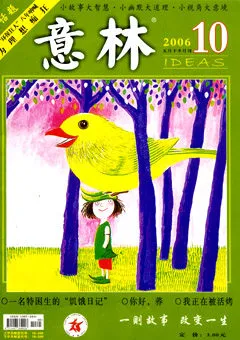沙那罕名琴
保羅·瓊斯
在我的一生之中,麥克舅舅的那把小提琴一直被視為持家的寶貝,只要它一天存在,這個家就有其維系的力量。我最早的記憶是在麥克舅舅第一次讓我親睹小提琴的時候。他掀開破舊的黑盒子,那把小提琴躺在華麗耀眼的綠色天鵝絨里。
“現在,你可以說真正看過一把名琴了。”他嚴肅地說,并且讓我從提琴兩側“f”形的洞中看到里面已經褪色的標記——格里摩那安東紐斯(意大利城市,以制作小提琴聞名)。史塔拉第瓦里斯名琴。
“這是一把頂尖的樂器。”
事實上,麥克舅舅不算是什么音樂家,而是水利局的職員,一位在附近廣受尊敬的、沉默的長者。舅舅可以說沒有拉小提琴的天分,而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是他父親把小提琴傳給了他。不費思索地,他父親自然又得自他祖父之手。依此類推可以溯源到最早把小提琴從意大利帶到科克來的老祖宗。麥克舅舅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親,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然而她總是喜歡把事情往最壞的地方打算。我父親相反的,一向非常樂觀。就因為如此,我家一直有兩股互相平衡的力量。父親是一個糕餅師傅,一個非常優秀、刻苦勤奮的德裔美國面包匠。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一直到自己擁有一家面包店。等他有了自己的店面以后,往往又會想把事業朝更大的地方去擴展。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母親。她老是擔憂著父親的那些遠大的創業計劃,害怕有一天我們會債務纏身而導致喪家毀業。在她的眼中,向別人借一毛錢不但是一種恥辱,甚至是一種可怕的危險。
父親最大的冒險是在亞撒斯街開店的那一次。
“我跟你說,瑪麗,根本沒有什么風險,”父親說,“只不過是在貸款契約上簽個字而已!”
“要貸款多少?”
“三千塊。如果順利的話,兩年之內我可以還清。我跟你說,那個地方真是一座金礦啊!”
“但是,萬一房子被抵押了,”母親哭喪著臉說,“我們會流落街頭,變成乞丐啊!查理。”
那天我們很早就吃過晚餐,全家都坐在餐桌旁邊。我在一個角落寫家庭作業,舅舅在左邊看晚報。此時,他取下眼鏡,合上報紙。
“聽我說,沒有比爭執的雙方各持一理而相持不下更糟糕的事。我想,也許我能解決這個問題。”
他站起來,把瓷柜上面的小提琴取下來。
“我聽說這種牌子的小提琴可以賣到五千塊錢。把它拿去賣了吧!查理。”
“哦!麥克!”母親說。
“我不能這么做,麥克。”父親說。
“如果你急著用錢,”舅舅對父親說,“可以在老艾瑞關門之前送去給他。”
說完之后,他戴上眼鏡,重新又攤開報紙。我發現他的手微微地在顫抖,可是他的聲音卻十分堅持。
“反正我也老了,不能再去動它了。”
因此,父親就挾著那把提琴出去了。不久門口傳來父親的腳步聲。他踏著快步,一面還吹著口哨。我們認定現在一切應該都妥當了。意外地,他進來的時候,手里卻仍然提著那個琴盒,而他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把它放回原處。
“這樣看起來好多了。”他說。
“你沒有把它賣了?!”舅舅問道。
“正當我要敲艾瑞的店門的時候,”父親說,“我忽然想到,為什么我們要賣了它呢?把它放在那上面,就好像一個里面有五十張百元大鈔的保險柜一樣。”母親立刻綻放出笑容,“我好高興哦!查理。”
“這還蠻有道理的,”舅舅平心靜氣地說,“如果真是這樣,我現在決定要正式宣布:在我的遺囑中,小麥克是這把提琴的繼承人。”
后來,貸款的償還并沒有發生問題,雖然比父親預定的期限晚了三年。高中畢業那一年的夏天,舅舅去世了,他的小提琴就到了我手里。當時我準備進入工程學院就讀,雖然家里的收入還無法供給我足夠的費用,然而瓷柜上面的琴盒卻使我深信一切都不成問題。
臨行的前一天,爸媽都在店里忙著,我帶著小提琴到了艾瑞的樂器行。老艾瑞從里面走出來,眼睛閃著像鷹隼般銳利的光芒。我把琴盒打開,向他展現我的提琴。
“這個值多少錢?”
他拿起小提琴,把它靠在厚厚的眼鏡邊緣。“二十五塊到五十塊之間,這要看是什么人出價。”
“怎么會呢?它不是一把史塔拉第瓦里斯名琴嗎?”
“它的確有這么一個標記,”他心平氣和地說,“許多小提琴上面都有,可惜都不是真貨。從來就沒有一把真貨!你這把大概有一百年的歷史,可是,請恕我直言,它不是一把頂好的貨色。”
他十分仔細地瞧著我,然后說:“我曾經看過這把提琴。你是不是查理·安格魯的兒子?”
“是的!”我簡單地回答。當然,我沒有把它賣了。當母親的眼光瞟到瓷柜上面的時候,她嚇了一跳。
“小提琴!”她用手按著胸口,“你把它賣了?!”這時候父親的臉上流露出一種憂慮的表情。我搖搖頭,回答她:“我想把它擺在學校的寢室里面,這樣也有個東西好讓我想起家里啊!”母親這時候便轉憂為喜。
“除此之外,”我接著說,“帶著它,你也可以放心多了。如果我急需要用錢,它就好像一個裝滿鈔票的琴盒,可以派上用場。對嗎?老爹!”“對的!乖兒子,對的!”父親說。他的眼睛卻一直故意瞧著其他的地方。
(劉可榮摘自《世界經典小小說金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