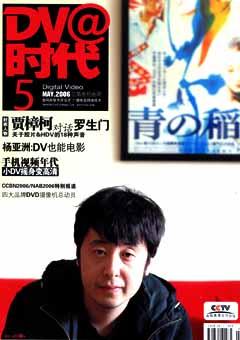DV的社會價值
一
DV的出現,帶來了整個記錄方式或者書寫方式的改變.也是民間紀錄片得以膨脹的重要技術基礎。隨著DV在中國的普及,現實題材作品不斷涌現,以紀實為主的DV紀錄片逐漸成了主流。以前的紀錄片工作者要扛著笨重的攝像機,有錄音、有照明、甚至整個劇組共同操作。《毛澤東》(1993)十二集大型文獻紀錄片的攝制耗資800多萬,《布達拉宮》耗資500多萬,(故宮)的總投入也高達500多萬,這些大成本大制作的“大片”,都投入了最強大的制作陣容和精力,所表現的社會意義也往往是重大的,領袖偉人.歷史性建筑,重大政治事件,如果考慮該年度人民幣購買力的折算,這些紀錄片的影像社會價值很難用金錢來衡量。但是在藝術民主化概念不斷深化的今天,我們會發現普通人的故事同樣感人,普通人的家庭住所一樣發生著扣人心弦的矛盾糾葛.這些人的社會價值意義也許會遜色于歷史偉人和故宮等,但他們的價值同樣擁有被保存的權利價值。
DV紀錄片的出現可以被看做是用低成本保存社會影像的一種手段,現在用“掌中寶”去紀錄一些事情,變得像用筆寫字一樣容易,更多人擁有了在社會中“說話”的權利。大量個體影像愛好者的參與,帶來了影像社會價值“官方表達”觀念的變遷,民間視點和個體表達成為了民間影像的最大特點。獨立性是DV區別主流媒體的主要特征,因此DV紀錄片的創作主體對社會價值的紀錄保持著一種公益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業余性和獨立性是相互依存.擁有了公益精神的職業影像人,必然喪失獨立性,走向商業影像和官方影像。歸根到底DV作品體現了一種民間文化的視覺狂歡品性。在這種視覺化的形象狂歡中,視覺形象本身不但顛倒了各種官方文化的原則和美學標準,而且具有全民性和廣泛參與性。
現在,已經有不少DV愛好者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主流媒體和精英紀錄片創作者所沒有凝視過的地方。紀錄歷史,紀錄社會光靠官方的影像部門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歷史和社會的組成本身,就是由無數個年代和無數個家庭組成的,沒有大眾化(DV)的紀錄,就不會有相對完整的社會紀錄。今天紀錄過的,明天就是歷史。這也許就是DV會在不遠的將來,在影像積累和海量儲存上超過官方影像的原因和價值。
二
社會如何被紀錄,紀錄什么?什么在社會中即將沉淪?民間影像紀錄的社會意義如何在DV中體現?這些都是擺在無數DV愛好者眼前急待解決的問題。過去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找到證人做采訪,做口述.而一旦見證人都沒有了,就會比較麻煩。筆者數年前曾經與幾位紀錄片同仁精心策劃過兩個跨時代的人物傳記紀錄片,一部是《最后一位太監》,另一部是《毛人鳳的“副手”》,不幸的是,當投資和撰稿都已到位時,這兩位曾經叱咤風云的人物卻分別以百歲的高齡依次逝世。這件事情本身對我的震動很大,因為在社會價值的保存面前,我們無數的一線紀錄片工作者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在現代社會,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每時每刻都會有富含自然的、環境的.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東西出現或者滅絕,由于我們人類沒有或者忽略了用影像紀錄保存,那么不用說我們的后人看不到,就連我們的“回顧”也會無從談起。
DV紀錄的大都是民間的小人物和大眾生活,如果我們拋開創作中的藝術和技術的不穩定因素和自然主義表現帶來的消極影像,這種趨勢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這些顯然是不夠的,DV還可以拓展自己更廣闊的空間:一切被官方媒體注意力所遺棄的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應該受到關注,這也許正是DV民間影像紀錄功能的魅力所在。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社會的歷史絕不僅僅是戰爭史,國家政治史,軍事史,領袖人物史和主流文化藝術的發展歷史。還有一些歷史是由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所建構的,只是由于中國千百年來的等級制度壓迫了這種大眾日常社會歷史的表現話語權——這種“平常人,平常事”歷史建構的需要,恰好與我在第一篇(DV的記錄價值)中所提到的DV影像的記錄價值不謀而合。DV影像可以在沉淪的大眾社會價值觀中找到突破點,以其低成本、易操作和隨意性成為紀錄大眾底層社會人物和社會生活的最佳媒介。因此DV富有這樣的歷史使命;紀錄有可能沉淪的卻是有價值的東西。什么東西富有價值?這便是因人而異了,在有的編導的眼中,搭臺唱戲的草臺班子富有價值,有的人認為同性戀具有人性價值,社會的價值在每個被攝對象身上都有著不同層次的體現,同時在不同的DV創作者眼中,他們都應該是肩有共同的構建大眾歷史層面的意義。
三
維護DV紀錄片社會價值的純正性依靠的是創作者的紀錄立場和道德良心。前文我一再強調,真實的內涵不在于你用紀實手法拍下來的就是真實,或者不用紀實手法拍的就不真實,紀實手法拍下來的很可能是虛假的,因為它更有欺騙性。我們探討真實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需要每個DV愛好者堅守這一底線,這也是唯一能夠保證DV作品社會價值擁有“真實價值”的權威保證。否則。我們就會喪失對DV的最基本的信任,紀錄片將喪失全部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當DV紀錄片面臨嚴重的信任危機和合法性危機的時候。DV的社會價值便會蕩然無存。
我們探討DV紀錄的真實性和探討DV作品的社會價值是一致的,就在于我們是要對觀眾建立信任感。DV人面對拍攝對象,要用一種謙虛的敬畏的態度,對真相負責,當然這并不排斥創作者的主觀篩選,提煉,加工,再創造,否則將會滑向自然主義和無意義的深淵。事實上當一部DV紀錄片成片之后,主創者的權威身份便消解了,他也僅僅是一個自身作品的旁觀者.至多作者這個特殊觀眾對作品的領悟更加獨到一些,更加全面一些。DV作品的更多社會價值意義的鏈條需要在一代又一代的欣賞者和接收者中去充實、完善。可見.我們對任何社會價值的詮釋都僅僅是當代的一種詮釋。時過境遷,同樣的DV作品會在不同時代的人們頭腦中顯現出迥異甚至完全相反的社會價值,只是這種體現在只有10歲的DV身上表現得并不明顯。我非常堅信,當DV步入成年發展期時,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些作品,一定會在當時所流行的價值觀,世界觀的引導下,擁有新的解釋。筆者的DV作品《伴》創作了5年,作品問世也有2年了,我在講課的過程中發現社會價值的多元化詮釋,在《伴》身上已經初見端倪。我在剛剛剪輯成片時,許多學生看了以為該片是敘述一位老而無養的老人與豬相依為命的故事也有人直指婆媳之間的僵硬關系是造成“豬為伴”的主要原因。到了今年,很多人對老太太養豬的看似愚蠢荒誕的行為進行了深度的詮釋,并有人寫書面評論,認為該片“反映了當代農村社會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人情淡漠,反映了當代農村生活中生存信仰的缺失和生活內涵的無意義”。這些豐富的社會價值都是筆者和其它創作者所未預料到的。相信若干年后,對DV紀錄片(伴)的社會價值的詮釋將會更為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