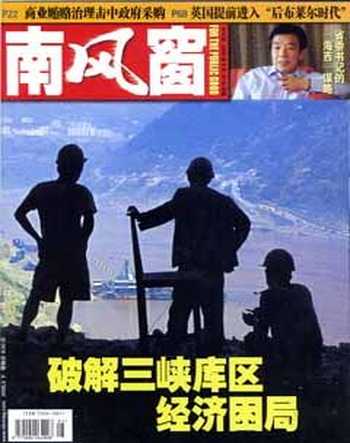有一種威權主義者
高超群
由于改革的艱難,人們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個自覺于自己的政治使命、凌駕于政治機構之上的權威,以其巨大的聲望、以非常規(guī)的手段排除這些阻力。
據(jù)說一個民族在心存希望而又在現(xiàn)實中屢遭挫折,幾乎陷入絕境的時候,就會產(chǎn)生對權威和巨人的渴望。在我們的改革年代里,對于權威的呼喚雖然并不強烈,但卻從沒有斷絕過。由于改革的艱難,人們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個自覺于自己的政治使命、凌駕于政治機構之上的權威,以其巨大的聲望、以非常規(guī)的手段排除這些阻力。畢竟,從經(jīng)驗看來這是最為省力的,而且也有現(xiàn)成的成功例子可循。但是這種期望中的權威并沒有出現(xiàn),而改革也就在摸索和自發(fā)中默默前行。
令人奇怪的是,近年來這種聲音卻越來越響亮,甚至越來越急切。經(jīng)過28年的改革,有一種人急不可耐地希望盡早搭乘上特權階層的快船。他們也感到了社會不穩(wěn)定的威脅,但是并不以為自己有能力能夠阻擋它的光臨。于是他們希望為特權抹上新的油彩,并再次說服人們接受、寬容、忍耐新的現(xiàn)實。他們私分了家產(chǎn),僅僅改換了不平等的形式,卻依然夢想著做永遠的家長。歷史和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沒有平等的憲政國家,其最終難逃威權獨裁與暴民的對峙、輪替;這恰恰就如同,沒有平等的市場經(jīng)濟,其最終也不過是權貴資本的樂園與土圍子式的假劣生產(chǎn)基地。
黑格爾曾經(jīng)說過:“地上實在沒有比一位君主給完全由他掌握的國家權力增補更廣闊的基礎更為壯觀的世間戲劇了。”在法國大革命以后的普魯士,權貴們反對承認變革的必然性卻在變革時死保自己占有的一切。在黑格爾看來,這是一種“軟弱性”,是一種恐懼心,無非是貴族浪蕩子的精神,和有志于變革的勇氣全然不同,其結果是不想部分失去占有,必然落得全部剝奪。
這種權威主義者,或者玩物喪志,或者自怨自艾。對稍微一點點的風吹草動都非常敏感。他們當中自以為有良知和責任心者寧肯不斷地自我責備、懺悔,也不愿意或者沒有力量干一點權威應該干的事情。通過自我嘲弄、互相譏諷、風言風語來消解心中的焦慮,來抵抗自己對權威地位的不適應。就像當年法國的貴族在沙龍里盡情地贊美平等、民主,卻絲毫不肯在現(xiàn)實世界里稍稍放棄自己為人所痛恨的特權。就像當年法國的文人,在革命來臨之前奔走呼號,但真正當革命落到他們手里的時候,他們卻因恐懼和慌張而實施恐怖,就像恩格斯說的那樣:“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統(tǒng)治幾乎完全要歸罪于過度恐懼的,以愛國者自居的資產(chǎn)者,歸罪于嚇破了膽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時期干自己勾當?shù)哪菐土髅ァ!?/p>
從18世紀末直到20世紀上半葉的革命浪潮,是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時代。英國、美國、法國、俄國、中國這五個現(xiàn)今仍然最有權勢的國家,恰恰是五大革命的發(fā)生地。這些革命歸根到底都是為同一種精神所驅(qū)使,都是為了實現(xiàn)“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都是受到人不再因為血緣、出身、財富、權勢的差異而分為尊卑等級,人作為人是平等的這樣一種觀念的鼓舞。人們可以很輕易地指責這些革命中所包涵的殘忍、血腥和破壞,甚至也可以很輕松地用那些背叛革命理想的言行來反駁說,平等只不過是個遮蔽暴行的幌子。但誰也無法否認:“平等的逐漸發(fā)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這種發(fā)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時每刻都能擺脫人力的阻撓,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它前進。”如同托克維爾所說,這場風暴要掃落世界上最后一頂王冠,否則絕不會停息。他甚至不無恐懼地道出自己所發(fā)現(xiàn)的真相:“企圖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個民族只有順應上蒼給他們安排的社會情況。”它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堅韌,一切其他的目標,國家的興旺、民族的復興、財富的增長、小康的落實、現(xiàn)代化的實現(xiàn)等等,都必須接受以它的實現(xiàn)為前提的現(xiàn)實。所有的權威必須以它為基礎,否則都是不牢靠的、虛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