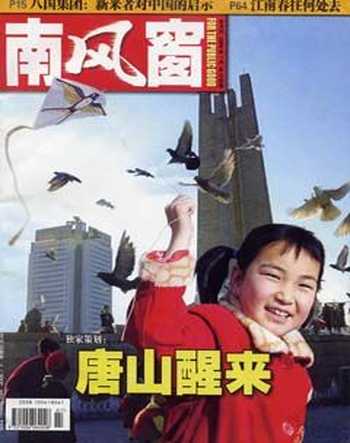房地產政策調控的產業之基
歐陽覓劍
通過比較上海和北京房地產市場的不同走勢,我們可以初步找到那些影響房價漲跌的產業因素。在這個基礎上制定的調控政策,會更有針對性,也更符合產業和市場發展規律。
調控政策起到效果了嗎?
這兩年,國務院及各部委發布的關于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幾個重要文件,基本上都以“穩定住房價格”作為關鍵詞,比如,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2005年4月七部委出臺《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2006年5月九部委聯合制定《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穩定住房價格”似乎成了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
但整體來看,以穩定住房價格為目標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尚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主要城市的房價仍然快速上漲,北京尤其突出。根據統計局的數字,這個地區2005年的漲幅超過上年,2006年第一季度漲幅再度提高,政策調控的作用適得其反。但人們并沒有因此而對政策調控的有效性進行反思,很多人仍然相信,政策調控可以解決房地產市場目前存在的問題。兩個方面的因素支持了他們的這種信心,一是在理論上,他們認為政策調控的力度還可以加強,那就有可能取得正面的效果;二是上海的房價去年開始出現下降的勢頭,似乎是證明政策調控可能有效的實例。但深入分析之后,我們會發現,上海房價出現轉折,并不是政策調控有效性的例證;相反,它證明了,政策調控并不是穩定房價的決定性因素。
2004年,上海商品住宅每平方米的平均銷售價格要比北京高出1000多元。2005年上海房價漲幅下降,下半年房價甚至同比小幅下降,而北京漲幅增加,于是北京房價超過上海。根據統計局的數字,上海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為6698元/平方米,而北京商品住宅期房均價為6725元/平方米。上海和北京的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不同的走勢,比較兩者的異同,我們能夠初步找到那些影響房價漲跌的因素。
很多人將房價快速上漲的原因歸結為投機者炒房、地方政府抬高房價和地價、開發商囤積房源、追求暴利,這些因素使房價不正常地上漲,因此,利用政策進行調控、抑制需求是正當而且必須的。但是,這些因素在上海和北京同樣存在,上海的情況只會比北京更為嚴重(溫州炒房團和外資炒房等與上海聯系更為緊密,上海地方政府距離中央比較遠),如果它們是房價上漲的主因,就不可能出現北京高漲而上海緩和的情況。有人認為,是政策調控在抑制了這些因素,使上海房價出現轉折,這是他們認為政策調控有效的理據,但同時實行的相同政策,為什么沒有在北京抑制住這些因素呢?
上海和北京房地產業的比較
上海和北京房地產市場走勢相反,其原因要在它們的差異性中尋找。這兩個地區的房地產市場最重要的不同,是它們的市場和產業發展的時間和程度不同。上海房地產業獲得較快發展的時間要早于北京,因而積累的資源也更多。上海房地產在1996年前后有一個飛躍式的發展,而北京要到1999年之后。
1995年,上海房地產開發建設的竣工房屋面積為700.39萬平方米,與北京的652.99萬平方米相差不大;但1996年,上海竣工房屋面積為1207.86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近一倍,而北京仍然與上年持平,只是663.41萬平方米;此后兩年,上海房地產開發建設的竣工房屋面積都是北京的兩倍上下;直到1999年,北京才從1998年的842.81萬平方米驟增至1208.5萬平方米,追上上海的1468.6萬平方米;此后幾年,兩地的竣工房屋面積都相差不多,北京在2002年2003年還比上海多。
上海在1996年到1998年3年間,比北京多積累了2000多萬平方米房源,這大致相當于北京現在一年的商品房屋銷售面積。這就使上海房地產市場的供給能比北京更充足,主要是形成了更加發達的二手房市場。上海二手房的成交量近20萬套,超過了新房的成交量,如果新房漲得太快,市民可以轉為購買二手房,這對房價的上漲起到了抑制作用;而北京二手房交易量只有7萬套,占住房銷售的比例不大,雖然二手商品房價格比較便宜,平均只是每平方米4000多元,但沒有能夠對新房的價格形成沖擊。
住房存量大,可供出租的房源也就比較多。相比北京居民,上海居民租到合意住房的機會也會比北京多,他們在租房和買房之間的選擇余地更大,這也能調劑對新房的需求,抑制新房價格上漲。
市場結構的豐富要以企業發展為基礎
市場和產業發展的時間較長,也培育了一批有實力的企業。上海1995年有1673家房地產開發企業,此后每年都增加幾百家,到1998年達到2601家。這么多企業擠在房地產市場,勢必發生激烈的競爭,優勝劣汰。1998年之后,上海的房地產企業數量不增反減,到2003年只剩下2100多家,這兩年在房地產下行的情況下,又有一大批企業被淘汰。留下來的則是那些能夠比較有效地控制成本的企業,在競爭的壓力下,它們能夠起到抑制房價的作用。反觀北京,1999年之前一直只有400多家房地產開發企業,到2003年才達到1000家,競爭程度顯然不夠激烈。
產業發展的結果,是使房地產市場的結構更加豐富。住房供應結構是這兩年調控政策的重點,但主要是對戶型(豪宅、大戶型、小戶型等)結構的規定。但房地產市場結構還包括區域結構(市區、郊區)、產品結構(新房、二手房、租房)。住房存量的增加,能使這三方面的結構都得到改善。還有一個重要的市場結構是企業類型,其他市場結構的轉變都要以此為基礎。企業的偏好和優勢各不相同,有的開發商偏好建設大戶型、在市區中心建房,它們的房子肯定會賣得貴;隨著需求總量的發展,市場會趨向細分,就會有一些其他類型的企業發展起來,它們能在郊區建造價格比較低的住房,為中等收入人群提供產品。
積累了住房存量和企業,房地產業的問題大部分都會得到解決或緩和。房地產市場的結構將更加合理,人們可以在買房和租房、新房和二手房、市區和郊區、大戶型和小戶型之間進行選擇。那樣,房價可以被抑制,而人們居住的質量會改善。
產業發展抑制房價上漲
上海的房價在2005年發生轉折,首先是產業的發展和積累的結果。房地產業的發展積累了住房存量(形成了活躍的二手房市場),培育了競爭的環境和有實力的企業,才抑制了房價上漲。因為這些因素,上海的房價今后幾年漲幅都不會太高,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進而,這些因素會壓縮投機的空間。投機者炒作新房,消費者就可以選擇二手房或者是租房,不會因為投機者制造的漲價氣氛而恐慌,被動推高房價。房價漲幅趨緩,投機者就無機可乘。在上海,一些溫州炒房者已經不是靠倒買倒賣獲益,轉而關注物業經營的收入。投機資本從來都只是追逐漲跌趨勢,而不能長期性地制造漲跌。
開發商因為競爭壓力,也就不敢囤積房源。當購房者能在不同開發商和不同樓盤之間進行選擇,囤積房子就意味著失去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源閑置帶來成本和風險,開發商不敢輕易為之。在住房存量比較大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也就沒有可能依靠高房價獲得高額土地收益。
如果說政策調控對上海房價的轉折有所影響,那也只是在產業發展的基礎上發生了作用,離開了產業的發展和積累,調控政策就起不了作用。
那么,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地區,解決房地產市場問題和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的根本,在于房地產業的長足發展。北京的房地產業發展比上海晚3年左右,我們可以期待,北京住房的性價比在兩三年之內會有很大的提升,快速上漲的勢頭將被改變,但我們不能急功近利地企盼這種情況立刻會發生。產業的發展需要時間,政策應該遵循產業發展的規律,而不能將它打斷。
產業發展為本,政策調控為輔
房地產市場問題的解決,最終要靠產業和市場本身的發展,調控政策只是起到輔助作用。我們要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當然也不是任由市場自然發展,因為房地產開發建設的周期比較長(建一幢住宅就需要兩年左右),企業有時不能根據市場信息及時調整投資,政府部門利用政策加以引導,或許能夠加快產業調整的進程。但這些政策,一定要以產業發展本身作為基礎和出發點,對趨勢的判斷和跟從至關重要。以此為原則,房地產調控政策應該在確定的界限內運行,不致對房地產業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中斷產業發展進程。
基于促進產業發展的目標,調控政策以抑制需求為重點是不合適的。目前的調控政策強調對需求的抑制,對擴大供給卻不夠重視。這也是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或許是因為習慣了短缺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環境,我們一直強調“需求側管理”,要求需求方忍受供給短缺。但現在已經不是短缺經濟時期,各產業的供給能力都能比較快地增長,在這樣的情況下,只需要抑制那些短期波動性的需求,而對于那些長期性的需求,則應當加以鼓勵和引導,同時促進供給的快速增長。北京、深圳等城市對住房的需求是長期性的,在這些地區,抑制需求會打擊居民改善居住質量的意愿,擴大供給才是長期的解決之道。從擴大供給和產業發展的角度看,更加不應該抑制需求,因為需求減少,預期銷量和利潤下降,就不會有大量資本進入房地產業,那樣供給會在一段時間內減少,市場競爭也會變得緩和,不利于抑制房價上漲和居民獲得性價比更高的居住服務。因此,調控政策應該是鼓勵、引導需求和擴大供給。
具體政策也應著眼于減少交易費用和擴大供給總量。目前使用的政策工具有三類。一是制定交易規則,維持市場秩序,例如調整住房轉讓環節營業稅,加大對閑置土地的處置力度,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信息系統和信息發布制度。二是政府參與市場交易,例如保證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土地供應,加快城鎮廉租住房制度建設,規范發展經濟適用住房。三是直接規定市場主體的行為,例如規定套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所占比例要在70%以上,規定商業銀行不能對哪些客戶發放貸款,規定90平方米以上的個人住房按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
直接規定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為了實現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的目標。以穩定價格作為目標,勢必會延伸到對產品和市場的結構進行管制,進而就要對企業的經營進行干預,規定它們提供哪些產品,不提供哪些產品。這是行政干預,看上去直接有效,但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而且難以實現,企業會找到規避的辦法,比如建造可以合并成大戶型的小戶型,監管的難度和成本非常高。這種政策工具雖然符合短期內的施政需要(比如加快銀行收回貸款),但從長遠看應該逐步取消。
制定交易規則是政策的首選工具,但在目前情況下,房地產業急需大力發展,提高稅率使交易費用增加,并不是非常適當。一般而言,只有對那些需要抑制發展的產業和市場,比如污染比較嚴重的產業,政府才應當提高其交易費用;而對于那些需要促進其發展的產業,應當盡量減少交易費用。
對于成熟的產業,政府應該退出市場,不直接參與交易,但對于發展程度還比較低的房地產業,政府參與市場交易可以擴大供給,使產業基礎盡快建立起來。建造并規范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是目前應當積極使用的政策工具。這對總量和結構兩個中介目標的實現都有推動作用,政府參與建房,既能增加住房供應總量,也因為政府以建造價格較低的住房為主,能夠直接有效地改善住房供應結構。
總而言之,房地產調控政策要從促進市場、產業、企業發展的角度出發,它們才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借助它們的力量,政策目標才能得以實現。在政策調控和產業發展之間,我們要以后者為本,前者為輔,制定政策時要有一定的耐心和信心,等待房地產市場和產業獲得長足發展,從而使居民可以持續地改善居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