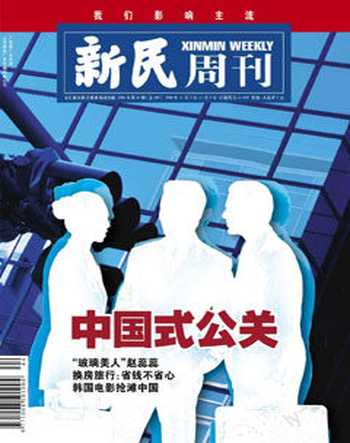不要被“通屬城市”所迷惑
周偉林
彼得·霍爾在其《城市文明》一書中,研究了跨時2500年(從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臘雅典到19世紀的巴黎等)中的20多個城市,發現這些城市在演化過程中都有一個很關鍵的10年到20年的時間。在這個時間里,城市發生了巨大變化:處于經濟和社會變遷中大量的新事物不斷涌現,融合并形成一種新的社會,他把這個時間稱為城市發展的“黃金時代”。在城市的演變中找到并推動這樣一個關鍵點非常重要,在我們身邊就不乏這種例子:清朝末代狀元張謇從1895年起到1920年,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做成南通的城市規劃;上海浦東自1990年開始至今才十多年時間,已經基本上由原來的農村地區變成一個嶄新的城市,為世界所矚目;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深圳?昆山等一大批城市。
眼下中國的城市發展正如火如荼進行,可以說政府?企業?市民構成了影響城市演進的三股力量。由于分權體制,地方政府承擔了過去由國家政府承擔的義務,轉而面臨越來越大的增加公共服務的壓力,這就使得許多城市在城市政府的政策中實現了驚人轉變,從管理主義變成“企業家主義”。這種企業家的態度把城市看作一種產品,需要在市場上售賣,而對交易的重視要求城市進行重建,以便吸引全球的投資者。加上政績考核體制的推壓,地方政府成了強勢的利益主體,它把城市的開發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無論出于就業?稅收?GDP增長?社會穩定或別的動機,都必須這么做。因此從政府的角度來講,這樣的動力一直是不竭而強勁的。觀察一下各地房地產市場的狀況,最不愿房價跌下來的,恐怕就是地方政府。在我國,土地是國有的,而農民的土地或者說“集體土地”,它用于開發也是最容易被征收的。另外比如我們買了產權房,可土地使用期是70年,商業用房40年,這之后呢?還是國家的,仍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的土地制度很早就決定了,不可能讓一個人私有土地永遠可以傳下去,所以政府先天就是最大的“地主”,并且通過城市化,一切資產的價值最后都將體現在土地價值上,屬于國家所有。
而企業選址,主要考慮成本因素。在運輸成本占總成本較大比重情況下,分別由資源導向和市場導向決定;在運輸成本只占總成本一小部分時,則取決于地方投入品導向,這涉及到當地的公共服務和舒適度。因此,無論是交通設施,還是其他投資環境,都會影響企業用腳投票。這就是列斐伏爾談論過的“空間的生產”:“我們可以見到公路?機場和資訊的網絡散布在空間中。在這個空間里,積累的搖籃?富裕的地方?歷史的主體?歷史性空間的中心——換句話說,就是城市——急速地擴張了。”“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線,都納入生產力與產物之中。”如此,動力是有了,然而結果呢?實際上,中國不少城市的發展今天呈現出一種讓人迷惑的獨特性:城市化的進程,在速度上在規模上在氣勢上也許都可詡為世界第一;而眾多城市的雜亂面貌和幾乎不講邏輯性的風格與樣式的拼合癥狀,可能也是無以復加的了。不妨看看我們所熟悉的不少城市,幾乎都在成為哈佛教授庫哈斯所描述的那種“通屬城市”(Generic City):一切“通屬”,兼容并有,無都市計劃可言,計劃了也沒有用,因為發展太快,沒有歷史的自覺,“過去”在我們的心目中越變越小。這種通屬城市的馬路只供行車,摩天大樓遍地皆是,互相也沒有什么結構關系,而行人被高架通道引入迷津(猶如在游樂場);無所謂地方特色,保存少許地方文物(或者是仿造)只是為了供旅游之需,這種城市最常見的生活標志就是機場和酒店。
最后,普通市民乍看起來無權無勢,其實他們體現著所居城市的性格。你若想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只有靠這個城市的人群的時尚生活給你靈感。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要人們注意到城市環境乃至居住方式對個人的意義。他說,一個家庭的居處,屋內的布置,烹飪的器具,日常的用具,以及房屋在地域上的分布情況,交織在家庭生活中,“它們極深刻地影響著家庭的法律?經濟及道德等各方面。不論住宅是高聳云霄的大樓或是不蔽風雨的篷帳,是富麗堂皇的別墅或是簡陋矮小的茅屋,一家的文化特性與其屋內的物質設備有著密切的關連……”
我國的“十一五規劃”,首次從過去5年編制一次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從“發展計劃”到“發展規劃”,一字之變,彰顯了和諧社會的城市發展和規劃,將遵循可持續發展?公共參與和公共利益至上?法制等原則,開始了變政府主導為以市場為基礎的政府?企業?居民互動的深層變革,這也許是開啟城市發展“黃金時代”的一個新契機。
(作者為復旦大學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