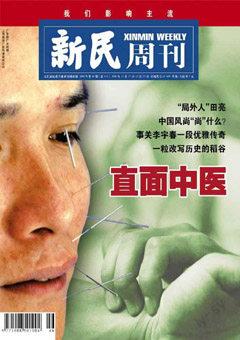中醫學生:徘徊在中西醫之間
于 芳
我希望中醫能作為一種醫學模式而存在,未來不會成為歷史學的一個小分支。然而,路在哪里呢?
人人都說學醫是件辛苦的事,學中醫更不易。大一時老師就說,60%的時間安排中醫課程,40%的時間學習西醫。這話一聽就覺得不合理,然而沒有人告訴你為什么。無窮無盡的疑問和矛盾,然而沒有人告訴你為什么。也許教授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三年課業,一年實習,還有一年花費在找工作上,而每一年都被這些沒有答案的“為什么”所折磨,但是卻不知答案有無,答案在哪里。這就是中醫學院的現實。
一進大學,初涉中醫知識就懵了:怎么會是這樣?幾年中學教育死記硬背的種種說辭言猶在耳,中醫學說首先和那些未經消化的中學知識打起架來:醫書說“精氣”是構成世界的本原,“精氣”到底是什么呢?唯物哲學認為物質是構成世界的本原,那么“精氣”是不是物質?中醫書的“陰陽”概念是有特定屬性的一分為二,與辯證法中的“矛盾”說能否印證呢?問老師,說不出所以然,給了一個答案倒是言簡意賅,與中學哲學教師無異:背。一遍一遍地背,背到條件反射一樣地接受“陰陽?五行?五臟?六腑?經絡”的概念為止。
然而第二學期開始學習西醫解剖。西醫的一套理論又完全把我們剛剛背熟的中醫認識顛覆了。中醫所說的臟腑和西醫所說的臟腑只不過在位置?命名方面有些相似,功能則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要把中醫的五臟心?肝?脾?肺?腎,六腑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和西醫的臟腑在一個醫學院二年級學生的頭腦中統一起來,是不可能的。中醫說脾具有主運化水谷?主升清?主統血的功能,但是西醫說脾是血循環中的重要濾過器官,具有濾血?儲血?造血和調節血容量的功能。你信誰?中西醫課程居然排在同一學期考試,考前復習的結果是中西醫在頭腦中打架,兩者都無法互相證明。恍惚中只想為混亂的思緒求得一個出路:常規都說中醫不如西醫科學,也罷,也罷,我也這樣認為算了——我竟然忘了,中醫將是我今后職業生涯的立身之本。
可是,不這樣又能怎樣呢?
醫學院里流傳一句話,“中醫的本科不如西醫的專科?中醫的碩士不如西醫的本科”,說的是中醫學生求職的艱難。乍聽尖刻,沒想到竟然是事實。令人瞠目的是,到畢業的時候我才知道,西醫院要的是西醫院校畢業的學生,而中醫院要的也還是西醫院校的學生:人們對于中醫院校畢業的學生看法很多,大多數認為“中醫不精,西醫不通”。考研還是改行:這是一個問題。但這其實是個偽問題。與我同年畢業的同學共計120人,做醫生尚不足40人。你問他們是不是做中醫?好問題。不過跟我之前的許多疑問一樣,這個問題也沒有答案。
我自覺徘徊在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之間,成了“邊緣人”。這與我接受大學教育的初衷相去甚遠,不禁尷尬乃至難過。然而,一旦以現代醫學作為唯一的標準,邊緣?尷尬乃至難過的,不只是我,中醫存在有沒有必要,似乎也變成了問題。一位學者說:“比如中醫,因為它高明有效,我們就說它是科學,但是一旦說它是科學,它就應該符合科學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學的也就是西醫的理論和方法去規范它。這種中西醫結合的結果就是現在中醫學院畢業的學生都不會號脈,最后必然使中醫消亡,只剩下中藥在西醫的體系中茍延殘喘或發揚光大。所以,即使從熱愛傳統文化的角度講,我也要堅決反對說中醫是科學。”這段話說得有個性,也有勇氣。但是很難解決現在的中醫教育和職業種種難題。我希望中醫能作為一種醫學模式而存在,未來不會成為歷史學的一個小分支。作為一個中醫學院畢業生,我說這句話,不僅出自“熱愛傳統文化的角度”。然而,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