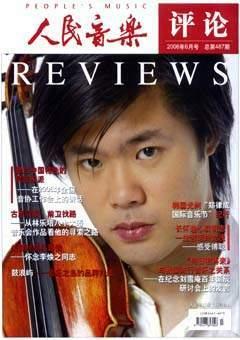用音樂抒豪情 為“海西”鼓與呼
由福建省文聯、中國音樂家協會創作委員會、《人民音樂》編輯部、福建省音樂家協會聯合主辦的“組歌《海峽西岸正春風》作品研討會”于2006年4月6日下午在福州舉行。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創作委員會主任、作曲家王世光,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創作委員會主任、上海音樂家協會主席、作曲家陸在易,《人民音樂》編輯部副主編、編審于慶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宋瑾,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省文聯副主席、省音樂家協會主席王耀華,福建省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陳濟謀,福建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邱守杰,以及福建省在榕的部分音樂家和有關媒體的新聞記者出席了會議。會議由福建省文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章紹同主持。
在福建省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陳濟謀同志代表主辦單位致歡迎詞后,大家聆聽了組歌《海峽西岸正春風》作品錄音,并請曲作者之一王耀華先生談了創作體會。
王耀華先生說,“海西”是洶涌著春光春潮的壯麗通道!“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舉措使地處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福建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身為生在福建長在福建的音樂工作者有責任為時代的突飛猛進、家鄉的日新月異謳歌。如何使這重大題材的創作以更為深邃的立意、開闊的構思、多彩的音樂語言來謳歌時代、謳歌家鄉,為“海西”鼓與呼呢?組歌《海峽西岸正春風》是一次嘗試、一次實踐。既要有時代的氣息,又要有歷史感;既要有較為深厚的思想內涵,又要有較為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這是這部作品構思的基本追求。為了實現這一追求,作品試圖以“春”為立意的契機,以“春”象征著無限生機,隱喻著蓬勃朝氣,內蘊著發展和活力。圍繞著“春”,構思了“春風”、“春雨”、“春光”、“春潮”。第一樂章《春風》,以開篇的磅礴氣勢,“沖門而進閩海闊,破門而出飛蛟龍”突出海峽西岸的生機、活力和朝氣。第二樂章《春雨》,以柔美秀麗的筆調與“春風”形成對比。第三樂章《春光》,以熱烈、歡快的筆調展現了明媚春光給人們帶來的爽朗情緒、深摯情懷,以及“雄視世界的自豪”。第四樂章《春潮》,以人心齊聚的萬鈞力構筑成氣貫長虹的“海西”豪氣,映射出 “又一輪春光留住亮麗的風景”。
民族性、時代性和群眾性三者的有機統一,是這部作品在音樂創作方面的努力方向。
其民族性的嘗試主要體現在旋律音調素材的運用、音樂結構的陳述方式和樂隊配器和聲的編配等。為了展現“海峽西岸”這一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感受,作品的旋律音調素材確定了以這一帶最具代表性意義的閩南民歌音調為主而兼及其它民族音樂素材的方針。
在音樂結構的陳述方式方面,作品從內容出發,適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更多地從中國傳統音樂借鑒了漸進式的、層層遞進的結構方式。
為了使整部作品的氣勢更加宏偉,在演唱演奏形式方面運用了組歌形式,即:以合唱隊和交響樂隊的合作,以及音樂主題的呈現、貫穿和展開來較為深刻地揭示作品的思想內容。但同時又根據音樂發展的需要,作品還適當地選用了部分中國樂器,如京胡、琵琶、嗩吶等民族樂器。并且在現代和聲的民族化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為了加強民族風格和水墨畫般清新的效果,和聲語言中常有一些五聲縱合化的大二度或四度疊置的和弦,或小二度附加音的風趣的色彩和弦,配器上趨于清淡,強調音色的變化。民族樂器和西洋樂隊的結合,民族打擊樂和西洋打擊樂的交錯運用,都增強了整部作品音樂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結合。
作品的時代性探索除了上所述及的對民族性、地域性旋律音調運用過程中的發展和改造之外,就是試圖探索適應時代發展,能表現新時代人民群眾精神風貌的音樂語言。
群眾性也是本作品試圖追尋的目標之一。組歌《海峽西岸正春風》的創作是體現“海西”這一重大題材的初步嘗試,但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
研討會上,與會的專家都認為這是一部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具有較高藝術水平的優秀作品,是為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鼓”與“呼”的成功之作。王世光說:“我覺得它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題材,它好像一張紙,唱的是海峽西岸今天的各個方面,但紙的背面確實承載著歷史的分量,是一個反映歷史內容非常豐富的作品,它著眼于今天,但也沒有割斷悠遠的歷史,同時它還展望著未來。這樣一個文藝作品需要大起大落、大刀闊斧的雄渾氣魄,引吭高歌的氣勢。我覺得在這里面選取了大型的管弦樂和大型的合唱這種形式作為骨架是非常好的。同時,在藝術的構思上和情感的設置方面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里面情調的搭配悠揚婉轉,多姿的節奏形式和表演方式等等的穿插豐富多彩。但是總體構思又是非常理性的周全和成熟。另外,從它的音樂構思和表達出來的東西來看,既有八閩大地的山川秀美,也體現了八閩大地文化傳統的精深。盡管我常常要求自己多學習福建的戲曲、民歌到各個方面的音樂,但畢竟由于語言的隔閡不像學北方的東西那么容易。從語言上入手進不去,那么對它的民間音樂神韻的理解就非常之難,肯定是皮毛。但是我認為,這個作品在表達它的傳統的民間音樂的同時,也照顧到了全國不同地域人的接受能力。”
陸在易說:“第一,這是一個非常可貴的題材。我完全贊成題材多元化的觀點。現在確實非常缺少這種現實題材,就是直接來寫我們正在變化或者是已經翻天覆地變化了的這個社會。今天這個題材就是“海西”這塊土地。一個音樂作品其實是一個藝術家長期對社會、對生活、對人生深刻感悟之后,集中體現為他的藝術語言的。所以在這個作品當中,我聽到了藝術家在這個時代當中深刻感悟的真誠心聲。第二,福建省文聯、省音協在上級領導的關懷指導下一貫地重視這方面的工作,我記得1990年《山海的交響》。我仿佛感覺到這個作品是在那個作品的思想、構思、追求下的一個延續,而且延續得非常好,無論從規模、深度、內涵各個方面來說,還是藝術上的高度、構思的精煉等等,要比《山海的交響》大大地進了一步。所以我認為福建省文聯、省音協在省領導的支持關懷下始終重視現實題材的創作,一直沒有放棄這個追求,這種精神值得各個省包括我們上海音樂家學習。第三,聽了這個作品以后就像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春風,這個春風有時給人感覺很清新,有時給人感覺很強勁,有時給人感覺很熱情,有時又感覺充滿了浪漫主義精神,充滿了幻想、憧憬,給人以思索,所以這個作品是一個有內涵的作品,不是淺白的。第四,這個作品從創作技法、創作手法上來說,很突出的就是簡潔、明了、樸素、不張揚,當然有時候也有“張揚”的地方,但是這種“張揚”并不是虛張聲勢,而是鋪墊,特別是到了后面要樂曲高潮部分來臨的時候,采取了“層層遞進”的方式;從音樂語言上來說是平易近人的,接近大眾的,所以這又是一個比較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作品,這么一個大型的、深刻的作品,近幾年來是比較少見的。第五,這個作品首先好在從開始部分到發展的過程都構思得挺好,其次我覺得這個作品不拘一格,在我印象中,以前這樣的構思還沒有遇到過。作為一個音樂作品,在長達一個小時的音樂演奏中,里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單從唱法上來說,有很多種唱法,有“黑鴨子”,有合唱,有領唱與合唱等等;有些間奏的地方銜接得很好,尤其是第三章《山海的交響》之后出現的那個銅管交響,很有意境。另外,冠以“交響組歌”的稱謂是否恰當?有待研究。”
于慶新說:“來之前我原以為這是一部‘應景之作,對其藝術水平有些疑惑,但聽了錄音卻出乎我的意料,感覺到耳目一新。我感覺作品在時代性、民族性、群眾性這三點上確實做得非常好。這個作品題材意義重大,音樂風格剛柔相濟,既有壯美也有柔美。壯美的地方氣勢磅礴,柔美的地方委婉抒情,感人肺腑。作品的民族風格濃郁。在形式上有合唱、獨唱,還有‘黑鴨子這種通俗風格的唱段。這段音樂比有的組歌中‘黑鴨子唱段寫得精彩,今后完全可以作為單獨聲樂作品來傳唱。另外,省委領導親自參與音樂創作,這一行動本身的意義遠遠大于作品本身。希望省委領導今后在福建音樂事業的發展上不只對聲樂作品的創作,包括民族器樂、歌劇、舞劇、交響樂等等方面都能給予大力扶持。提幾個建議:第一,京劇唱段的合唱音色不統一,是否考慮用‘國交合唱團,當然要注意戲曲風格的把握。第二,《情緣》一曲后半部分打擊樂器的配置使伴奏風格往流行音樂風格上靠,前后不夠統一。第三,整體布局上后半部較重,容易造成聽覺疲勞。另外,是否冠以‘交響組歌?這個概念比較模糊,不一定非要冠以‘交響才說明作品有交響性。”
宋瑾說:“這個作品總體給我的一個感覺就是一個‘和,這個‘和有幾個方面:第一個‘和是音樂和社會的‘和,音樂的立意與海峽西岸經濟戰略相統一。中國傳統最古老的和有和諧、相生相克,最后達到一種動態平衡的恰到好處等等。‘和首先是不同,對不同的東西,通過平衡達到一種‘和。春的意象用得很好。第二是政治和藝術的‘和。國家領導人希望藝術還是能為政治唱主旋律,如果音樂能夠很好地為藝術以外的社會等等服務,這本身就是一個研究領域,這個作品在這方面做得很好。第三是歷史與現代的‘和。這部作品雖然有時代性,但是又有厚重的發展的歷史感。不管從歌詞到音樂形式,這部作品是福建老、中、青這幾位作曲家合作的,作品既跟傳統有關系,也具有現代感。第四是中國跟西方之和。新音樂道路決定這部作品是在新音樂整個二十世紀上延續的,用西方的交響、管弦樂隊與中國的民族風格,包括福建本土風格的統一。包括在樂器的選用上,音樂語言本身的發展手法上延展性等等。第五是雅俗之和。因為曲子是群眾性的,可是交響是高雅藝術,所以雅俗這個方面做得很好。這部作品還不能用純藝術的尺度來衡量。我想能否在幾個不同上再作得好一些:一個是《聽雨》的持續音怎么處理更好些,再一個美聲跟通俗樂隊的關系怎么處理得更好些,另外,春光的意向跟間奏的音樂怎么合,《山海的交響》錄音女聲太亮,這個作品的收束感很強,可以用樂器把收束感淡化一下。”
福建省音協顧問、作曲家郭祖榮認為,這部作品在福建音調的運用上消化得很好,既運用了福建傳統民歌因素,又不是生搬硬套,曲調很新鮮。
福建師大音樂學院院長葉松榮教授說:“這部作品的整體構思、作曲技法、旋律語言等等,都有其不同凡響之處。這部作品的特色,第一,史詩性與戲劇性的統一。音樂具有壯闊的激情,宏大而嚴謹的結構,猶如一幅歷史畫卷,戲劇性地展示了海峽西岸的風光、人物、事件,音樂既跌宕起伏,又委婉細膩,有比較、有對應,富有情感張力。是一部融史詩性與戲劇性于一體的力作。第二,時代性與地域性的統一。組歌具有很強的時代特性,反映了當代福建人民的心聲,可稱為時代的最強音。這部作品又有鮮明的地域性,是因為這部組歌的音樂之根是深植于福建傳統音樂文化的土壤中,樂曲主要部分選擇了閩南民歌音調《燈紅歌》與《四季歌》為主題,除此之外,‘福永安寧(齊唱)的閩劇音調特色,‘福娃娃(童聲合唱)晉江兒歌音調素材的運用等。作者在追求時代性的同時,融進深厚的地域特色,使得二者互為映襯,為這部作品注入強烈的時代氣息和鮮明的地方特色。第三,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一。作品抒發兩岸人民同根同宗同胞情。藝術表現上,情真意切的旋律,完美獨特的結構形式,更為重要的是:在福建地域音樂特色基礎上各種藝術手法的運用,達到了和諧完美的統一。第四,個性和社會性相統一。組歌《海峽西岸正春風》作品具有鮮明的個性化音樂形象(這與其地域特色分不開),不雷同他人,也不重復自己,它源于傳統,又異于傳統;作品又有很強的社會性,作者出于社會責任感,對作品的社會效果有所考慮,比較符合大眾潛在的審美心理和審美基礎,音樂語言通俗易懂,有較強的可聽性和可接受性。”
福建省音協秘書長魏德泮說:“唐代詩人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組歌《海峽西岸正春風》就是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牢牢把握時代脈搏,貼近人民群眾的審美需要,用音樂的文藝形式生動展現福建人民改革開放、團結一致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精神風貌的優秀作品,是福建音樂工作者以實際行動響應省委號召,為全面形成‘風正氣順,人和業興良好趨勢做出的應有貢獻,這是時代的主旋律,人民奮進的號角,必將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作用。”
魏德泮 福建省音樂家協會秘書長、一級詞作家
(責任編輯 于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