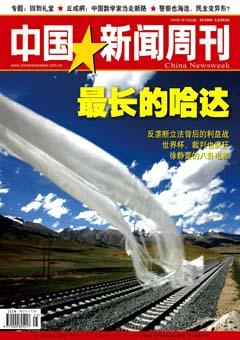審計風暴“轉型”
李中旭
民眾認為,“不點名”是一種退步;業內人士認為,“不點名”是一種進步。究竟孰是孰非?
“中央9個部門吃空額;18個部門挪用專項資金為私用;7個部門隱瞞收入、虛例支出,將資金私存私放”6月27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做中央預算執行審計情況的報告時如是說。每年6月底,“鐵面審計長”的這個報告,都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例行會議的重頭戲。2002年以來,由于“審計風暴”深入人心,李金華的報告已經成為民眾的心理期盼。
但是,在李金華讀完今年的報告之后,民眾的心理卻有落空的感覺。因為牽扯到上述違規行為的中央部門并沒有被點名,眾所期盼的新一輪“審計風暴”難見蹤影。兩天以后,時事評論員時寒冰在《上海證券報》發表時評,稱“審計報告不點名不利于審計監督”。
同時,今年的審計報告還向其他例行報告靠攏,先說成績后說不足,改變往年只說“不”的局面,導致今年報告比往年更長。
這些表面上的變化,盡管令民眾難以理解,但在業內人士看來,卻有著“轉型”的意義。“此前,對違規問題的查處是審計工作的重點,現在,這一重點正在向績效審計過渡,是一種進步”,中國審計學會理事、武漢大學商學院教授廖洪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雖然有轟動效應,但違規畢竟是少數,績效審計才是日常審計的重點,這一轉型也符合國際潮流。”
不點名是一種妥協?
“審計風暴”最為猛烈的2004年,也是各個部門反彈最為強烈的一年。據本刊不完全統計,前年的這個時候,云南大姚地震災區相關部門、錦州交行和法院、國家電力公司、長江重要堤防隱蔽工程建設管理局紛紛對審計報告提出質疑,或為自己找出開脫的理由。
后來,財政部、發改委、教育部、交通部、國家體育總局等一大批國家部委也被一一點名。“相對于地方,這些中央部委的反彈雖然沒有見諸報端,但影響力更大”,一位審計學者告訴本刊,“審計署不僅壓力很大,風險也不小”。
“現在一年查五十幾個億的違規資金,以前也不是沒有,只不過,前幾任審計長的時代,還沒有向全國人大做報告的規矩,都是內部報告”。中國審計學會副會長張以寬說。
盡管李金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報告時已經強調,將用公告制取代現在的“總報告點名制”,但外界普遍認為國家審計署將重回內部查賬的老路。6月27日以后,多名國家審計署官員受到問詢:你們究竟想怎么搞?
一名國家審計署官員為此詳細講解了目前實施的公告制的由來:2003年,公告制就已開始部分取代點名制的功能。點名制的好處是,社會影響力大,媒體跟進迅速,能夠在短時間內形成合力,有助于違規問題的整改,甚至從長遠來看有助于審計體制的變革。但是,點名制的弊端在于,李金華審計長不可能在有限的總報告篇幅內點出所有違規部門的名字,而有選擇的點名,顯然沒有堅持一視同仁的原則,本身就有些不公平。況且任何一項審計都將形成單一的審計報告并公布在國家審計署的網站上,較之點名制更為詳盡。就在李金華在全國人大常委做報告的前一天,對中國農業銀行的審計報告被公之于眾:違規存款業務142.73億元,違規發貸276.18億元,違規辦理票據業務97.18億元,3名省級分行行長被免職。
“因此,公告制較之點名制,是一種進步。”這位官員說。他告訴本刊,這一做法,仿效了美國審計總署的操作模式,該國的分項審計報告,民眾可以上網查詢,也可以查閱報告副本。
可以預見的是,今年分項審計報告還將包括青藏鐵路環境保護審計以及開發區財政稅收政策審計,無論是環保還是開發區,從前都未進入過審計總報告。“此前,國家對環保和開發區問題上的審計力度一直不夠。”廖洪說。
重點轉向績效審計
據張以寬回憶,國家審計署成立之初,國務院對審計署的要求是:全面審計抓重點。這個重點,就是加大對違規問題的審計力度。
在“審計風暴”進入第5個年頭的時候,違規行為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得到遏制,用李金華在今年報告中的話來說:“總的看,財政部在具體組織200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過程中較好地履行了職責,中央預算編制的質量、執行的效果和預算管理水平進一步提高。
這次審計查出的2005年度新發生的違法違規問題金額8.65億元,僅占審計當年資金量的0.6%。”
從違規審計到績效審計這一轉型,李金華在去年就有所提及,對違規和績效審計的比例大概為“一半對一半”。
“績效審計是一種非常科學的管理模式”,全國高級審計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北京工商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趙寶卿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錢怎么花的,花出了什么效果,只要一審計,立竿見影,較之其它方式的考核,這種考核方式的論據更為充分”。
轉型中,和績效審計一起獲得加強的,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經濟責任審計。績效審計對事,也是世界通行的審計規則;而經濟責任對人,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主要是考慮到,中國的一把手干部更多為任命制,具有較大的權力,對他們進行經濟責任審計,有事半功倍之效。”廖洪說,“1986年開始施行的廠長經理離任審計,是今天經濟責任審計最早的雛形。”
不過,到目前為止,因經濟責任審計落馬的高級官員尚未見諸報端。但據本刊了解,國家審計署在經濟責任審計方面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重點轉向績效審計和經濟責任審計之后,審計部門的工作量驟然加大,對常規問題的動態追蹤顯然比重點追蹤更加費時費力,也使原本人手緊缺的難題雪上加霜。
另一個讓人不平衡的對比則是,國家審計署的公務員總量只是美國國家審計總署的1/10,難免在做績效審計和經濟責任審計時捉襟見肘。
審計體制變革任重道遠
在審計工作重點轉型之際,審計體制的變革已經不是媒體熱評的焦點。相對于兩年之前“審計風暴”最為猛烈的時期,加強財政預算監管強化上游監督以根除審計風暴、將國家審計署列入人大序列來加強橫向監督等建言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兩年前,和教育部前副部長張保慶一樣,國家審計署前副審計長項俊波在調離審計署之前,也提出了設立國家審計院的構想。
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張以寬還提出了開展對政策進行事前審計的建議。他舉例說,美國在對政策的事前審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果我們西學中用,將對一些正在出臺、已經出臺的政策,比如公車改革的合理性等做出科學的界定。
“學界的上述共識,暫時還沒有獲得采納。”張以寬和趙寶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這一背景下,廖洪等人仍然在堅持審計體制改革“兩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全國審計系統垂直管理以根治地方保護主義;第二步,將審計部門列入人大序列。“我們還沒走第一步,怎么能奢求第二步呢”。廖洪對本刊說。
這兩大步雖然沒有邁出,但并不意味著決策層沒有預熱。今年6月1日,修訂后的《審計法》出現了多處重要變化。例如,新《審計法》第四條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每年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審計機關對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
審計工作報告應當重點報告對預算執行的審計情況。必要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對審計工作報告作出決議。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將審計工作報告中指出的問題的糾正情況和處理結果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
“這一前所未有的規定,強化了人大對審計工作的介入力度”。廖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