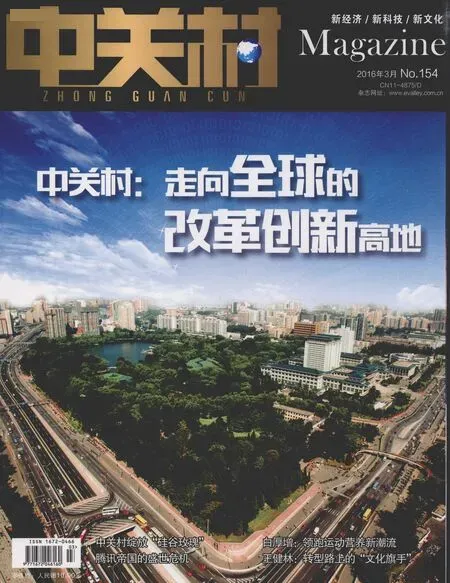MBO:上演了一出“捉放曹”
關 純
國有大型企業MBO(管理層持股),在短短的8個月時間里,上演了一出先禁后放的“捉放曹”。
人們還記憶猶新,去年5月國資委對MBO之“禁”事出有因,發端于“郎顧之爭”及由此引發的“保衛國資大討論”。老百姓對國有資產的驚人流失,痛心,愕然,憤慨;輿論對“權貴”們不擇手段地侵吞國資行為,予以抨擊撻伐。在這樣的氛圍中,代表國家利益的國資委下達了一個深得民心的“MBO禁令”。
殊不料在“MBO禁令”貫徹8個月之后,國資委在《關于進一步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實施意見》中,又傳出了“MBO禁令”的“解禁令”。平心而論,國資委對MBO的“禁”與“放”凸顯了國企改革“難于蜀道”的現狀。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難免“五里一徘徊”,需要不斷地總結經驗,逐步完善。因之,“禁”有原因,“放”有道理;此一時,彼一時,更何況“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人們也就不必過于驚詫了。只不過是國資委“朝令夕改”和“朝三暮四”的做法,似嫌不夠慎重,讓老百姓“腦筋一時不能急轉彎”,著實難以適應,也需要有個過程。
MBO畢竟是舶來品,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是成功的管理模式之一。我們采取“拿來主義”,借鑒應用,當然可以。但必須注意的是:西方實施MBO的企業通常是“私企”,盡管也有少量不承擔贏利職能的國企,只提供公共服務,管理成員卻沒有持國有股一說。我們的MBO完全是公有制下的“公家人”,倘若在持股依據上不能作到“字字有來歷,處處有根據”,說不清,道不白,則難免有“侵吞”之嫌。個中道理,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郎咸平教授都說得很清楚了,毋庸贅言。
應該說國資委《關于進一步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實施意見》,已經對實施MBO的程序規定,字里行間都充滿著嚴厲和謹慎。倘若嚴格執行,竊以為可以制止國有資產“放水”般的流失。但是我們的國情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正如我們每次學習黨和國家關于反腐倡廉的文件都熱血沸騰,充滿希望;然而,現實是仍然有為數不少的干部以身試法,黨風依然嚴竣,甚至老百姓譏之為“前腐后繼”。時有發生的“公有巨貪”,用古今中外的任何“游戲規則”來衡量,都是不允許的,可是“貪官”繼續存在,看來不是一紙條令能就范的。應用MBO的管理模式是有條件的,我們和西方的制度不同,這正像氣候、土壤、環境不同,如果照搬,難免發生“淮橘成枳”的后果。
多年來的改革實踐告訴我們,“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幾乎成了規律。此次MBO在短短的8個月的時間里“一捉一放”,“捉”也匆匆,“放”也匆匆,難免讓人擔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覬覦國有資產的人照樣會花樣翻新吞吃“國資”。因為他們更清楚,隨著各項改革舉措的日臻完善,“尋租”的機遇越來越少,難免最后猖狂地一跳!一位資深的傳媒人說,“事實上,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即便禁令之下,隱性的MBO仍在悄然進行。譬如,這幾年流行國企到國外實施戰略投資,相應出現大量國資在海外市場‘蒸發的案例還少么?這中間相當一部分難道不是被隱性MBO掉了么?請各位看官注意,明火執仗叫侵吞,暗渡陳倉何嘗不是侵吞?”
可見,MBO上演一出“捉放曹”仍然不能化解國有資產流失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