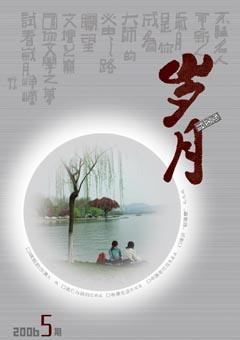老家的鄰居
李廣生
左 鄰
我家的左面,原來是生產隊的場院,四周是高高的土墻,中間是一塊足球場大小、坦蕩如砥的空地。記憶中,場院里總是堆滿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柴草和糧食。于是,在那個貧瘠的年代,在一個個風高月黑的夜晚,我常帶著幾個弟弟從墻上事先挖開的豁口魚貫而入,弄些東西來填飽肚子,燒熱那間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的老宅。
那時,看場院的是一個白胡子老頭,姓韓,樣子長得很兇,從來沒有笑模樣,一天從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手持粗壯的木棍圍著糧垛和秸稈垛巡視,稍有風吹草動,便大喝一聲,于是顫巍巍的棍子下便魔術般出現了一個鼻涕一把淚一把口袋里塞滿了麥穗或者谷粒的小孩。
場院是我和鄰家小孩的一個好去處,我們常鋌而走險地在看場院老頭的眼皮底下神出鬼沒地在麥垛里捉迷藏。上百個雷同面孔的麥垛,人鉆進去,是很難找到的。記得有一次,我鉆進麥垛里很長時間,也沒有被千呼萬喚的伙伴們找到,最后竟然在里面睡著了,睜開眼睛時已是暮色蒼茫,只見麥垛縫隙里篩進來的斑駁月光和咄咄逼人的蚊蟲,這才驚恐著賊一樣逃回家去了。
我十分喜愛場院,在幼年的記憶里,它已經成為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天上學、放學,總習慣于從場院外的土墻下走過,腳下是綠茸茸的小草,耳邊是蟈蟈悠長的鳴叫,鼻中是麥子悠悠的清香,天是那樣藍,陽光是那樣燦爛,風是那樣輕柔,我們所經歷的一年四季也好像只有通過場院才能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有的時候,討得看場院老頭的允許,我們還可以在里面尋些螞蚱或者蚯蚓給雞吃,因為聽老人講雞吃了這些東西會下雙黃蛋的,盡管很少吃過雙黃蛋,但我們仍是樂此不疲。有的時候,我們還常在場院里用水灌螻蛄或者田鼠,螻蛄十分有趣,常常一瓶水還不到,就舉著一雙黑色的鐵鉗繳械投降了。田鼠倒是狡猾得很,因為是收獲莊稼從田地里帶回來的,因此有幾分城府和野性。一個洞常有幾個出口,即使將一桶水灌下去,也不見它的蹤影,卻只見旁邊的壕溝里溢出水來。有的田鼠即使被堵個正著,渾身濕漉漉的浮出水面,但仍是一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樣子,尤其是那雙因絕望而冒著兇光的眼睛讓人不寒而栗。因此,小伙伴們很少伸手捉它,或者一鍬拍死,或者澆上煤油一把火點著,弄得田鼠“吱”的一聲沒了蹤影,片刻的工夫便見場院內的一個柴草垛濃煙滾滾,于是惹禍的孩子們“哄”的一下作鳥獸散。
場院在我的印象中,尤如一幅靜穆的田園山水畫,畫中布滿了古典的事物,轆轆井、石磨、高高的麥垛,還有看場護院的老人,即使許多年以后深入了城市的浮躁與繁華后,回想起場院來,內心里總是蕩起一絲甜蜜與苦澀的漣漪。
后來,生產隊解體了,我家東面的場院就變成了一塊塊趙錢孫李的宅基地了。再后來,一戶姓蘭的人家在我家的東面建起了一棟磚房,成為我家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左鄰。蘭家的老頭人瘦得很,皮包骨頭,胸前的一副花鏡夸張地炫耀著智慧,手里的一只臟兮兮的茶壺總是冒著熱氣。然而在我的記憶里,我家的東面好像永遠沒有這戶人家的存在,永遠是那個寬敞、親和、堆滿豐收和喜悅的場院。
右 舍
我家的右面,原來住著兩戶張姓的人家,三間土房,各住一半,共用一個灶房。兩戶人家好像有些血緣關系,一個稱兄一個道弟,關系處得十分融洽。
稱兄的是一個瞎子。從我記事時起,他好像總是成年累月地披著一條臟兮兮的被子,蜷縮在一截很少見到陽光的土炕上,目光空茫而渾濁。張瞎子既懶又饞,除了偶爾到戶外曬曬太陽,其余任何時候都不出屋,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從來不做,而且還常向女人要些好吃的,于是常見張瞎子的女人到街上用幾個口挪肚攢的雞蛋換回一個紙包紙裹的麻花給張瞎子吃。張瞎子的女人很能干,人雖長得瘦瘦的,可走起路來腳下生風。張瞎子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最小的女兒大我兩歲,我們一個班,她因個子最高當了班長,我則因一口氣能數130多個數而做了學習委員。我們是同時入學的,記得入學那一天,還是張瞎子的女人帶我和她的小女兒一起去學校報到的呢。
后來,我考學離開了故鄉。聽人說,張瞎子早已去世,張瞎子的女人和女兒也不知哪里去了。現在只留下張瞎子的兒子一個人在村委會的一間空房里孤獨地生活著,而且眼睛也已失明。
道弟的是一個車老板,一年四季總是穿著一件灰黑色的衣褂,嘴上叼著一支自卷的旱煙,臉上總是不見笑容。四匹膘肥體壯的馬拉著一掛墩墩實實的車架,大鞭子一甩嘎嘎地響,神氣得很。有好多次我去野外挖苣荬菜割豬毛草想搭他的車,可是每次都被他冷冷的目光和嘎嘎響的鞭子嚇退了念頭。車老板的女人是一個典型的鄉下養尊處優的女人,我們都叫她四娘。四娘高高的個子,短發,嘴皮子很厲害,鄰居們都懼她三分。盡管如此,我們兩家處得還是很不錯,走動也很頻繁。但自從四娘家在我家的右面搶前幾步蓋了三間一面青的新房后,我的母親和四娘的身體就非常的不好,總是鬧病,于是有人說我們兩家的房子犯說道,按風水先生的說法,左青龍右白虎,虎是不能壓住龍的,否則就會出事的。于是,母親從生產隊弄了一個犁鏵放在了我家房頂的西側,光芒霍霍的鏵尖直沖四娘家而去。四娘也不示弱,在自家煙囪上安上了一面鏡子,把妖魔鬼怪都擋在了房子外面。因為這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兩家鬧得很僵。但是大人之間的爭斗并沒有影響我和四娘的兒女之間的感情,我和四娘的兒女們常在一起玩過家家摔泥泡騎官馬殺官仗的游戲,一截矮矮的土墻覆滿了我們童年貧乏的歡樂。
后來,母親和四娘一天天老了,兒女們一天天大了,她倆之間的爭斗也一天天少了,來往也一天天多了。有的時候母親也叫我翻墻送些新蒸的饅頭給體弱多病的四娘,車老板也時常熱情地把去自留地鋤草的我們讓上他那威風的馬車捎上一段路。再后來,我家屋頂上的犁鏵和四娘家煙囪上的小鏡子都不見了蹤影。
如今,母親、四娘和車老板都遠離了這個喧囂的塵世,在那片叫西甸子的荒原上靜靜地沉睡著。而我和兄弟們以及四娘的兒女們則奔波在故鄉和故鄉以外的土地上,辛勤忙碌,生兒育女。昨天聽弟弟來電話說,四娘的大兒子正與父親商量兩家共建一棟磚房,共用一個間壁墻。兩個人還常在一塊兒搓搓麻將,有時候也喝上幾盅,然后嘮叨起那些發黃的略帶苦澀的往事,沒完沒了,直到深夜。
前院
我家的南面,也就是前院,有兩戶人家,一戶姓張,一戶姓胡。
張姓人家一家人都很內向,很少吱聲,所以來往并不多。因為我家的菜園與張家的后菜園僅一墻之隔,因此我們兄弟常偷窺張家的勝利果實,有的時候也順手牽羊飽餐一頓,當然之后便有吃不著葡萄的人告發到母親那里,于是免不了一頓皮肉之苦。
張家的大兒子人長得很精神,常見他身著一件軍綠色大衣,威武地端坐在一架驢車上,走村串屯放映電影。那個時候我好羨慕他的小弟,每場電影都落不下,而且不像我們常常為了一場電影而跋山涉水走很遠的路。每年的春節期間,張家的大兒子都會出現在村里組織的秧歌隊里,搖身變成《西游記》中那位會念緊箍咒的唐僧,帶著尚、孫、曹三位村民扮成的徒弟,身披袈裟腳踩高蹺在大街上和人群中騰云駕霧,煞是威風。
胡姓人家的家境與我家差不多。胡家的伯伯與我父親原來都在一個生產隊。父親在隊里做會計,整天與“噼啪”作響的算盤打交道,日理萬機一絲不茍地加減乘除。胡伯伯在隊里做“打頭的”,樣樣農活都拿得起來放得下,無論干什么活兒都始終沖在最前面,身后始終跟著千軍萬馬。因此,那個時候的我對胡伯伯敬佩得不得了。
胡家的幾個孩子都很淘氣,從早到晚唧唧喳喳房前屋后地跑來跑去,從未見過他們消停的時候。他們當中的胡三,也就是在四個男孩中排行老三的與我們很合得來,常與我們一起玩“拍釘子”的游戲。他跑的姿勢十分特殊,肚子使勁往前腆,腦袋拼命地向后仰,速度驚人,除了我之外,很少能有人抓到他。后來,胡三十三歲那一年,得了一場大病,據說是劇烈運動之后喝了大量的冷水“炸肺”了,后來就病死了。出殯的那天,我見到了躺在一張白木板上臉色鐵青的胡三,樣子哀憐而恐怖。從那以后,我們很少再玩“拍釘子”的游戲了,因為我們很怕跑累了喝冷水得病死掉。
現在,張姓人家已經搬走,據說仍住在鎮上,但我已好多年未見他家的人了,只是常常想起放露天電影和扭秧歌的儀表端莊的唐僧。胡姓人家仍住在我家前院,上次回老家見到胡家的老二,得知他們兄弟幾個都娶上了媳婦,日子過得也很富足。
后院
我家的北面,也就是后院,住的一戶人家姓王。當家的在公社里當干部,據說是“四把手”,因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所以我們都叫他二伯。二伯人長得精神,高高的個子,嫩嫩的皮膚,一件雪白的襯衫常年扎在褲腰里,走路說話十分有派。
因大人之間地位的差異,所以平日里兩家很少來往,我們見了二伯也大都是低著頭很少說話,即使說話,臉色也都脹得通紅,好像偷了人家東西似的。倒是二伯的老父親人十分好,說話也很幽默,一件黑色大褂上縫著兩個寬寬大大的口袋,里面總是裝滿了誘惑。因為每次老人來我家,都會先拿出些好吃的來,招惹兄弟幾個搶著翻他的口袋,甚至有一次,口急的小弟還撕掉了老人的扣子。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老人從家中偷著拿來十幾個肉餡餃子,那餃子香得很,流出的油把包裹的紙都浸透了。于是乎,早就按捺不住的兄弟們一擁而上,片刻的工夫,老人的手中就空無一物了。在我的記憶中,那頓餃子是我從小到大所吃過的最香的餃子了。
二伯有個弟弟,排行老四,因為智力有些問題,人們都叫他傻四。傻四很能干,一年四季手持一把掃帚或鋤頭,不知疲倦地清掃著院子,伺弄著園子里的莊稼。在我的印象中,從未見他歇息的時候,但總是因為活兒干不對頭,而遭到老父親的呵斥。有時我們也拿他開心,出一些腦筋急轉彎的題,或嘲笑他幾句,可是每次還沒等話說完,就被舉著掃帚的傻四追得狼奔豕突,但即使攆上,傻四舉起的掃帚也不會落下,只是橫眉立目地嚇唬我們一下,也有膽小的哇哇地哭個沒完,于是傻四又免不了被老父親扯著耳朵拽回屋了。
如今,二伯的老父親、母親和傻弟弟都已過世了,兒子出國留學后定居在美國加州,二伯夫婦則與女兒在省城哈爾濱過著滋潤的生活。
我常與二伯通話,可是每次都會被二娘搶斷,惹得二伯在旁邊直發火。當然我們聊得最多的還是老家的那些鄰居和鄉里鄉親,每次撂下電話的時候,都會隱約聽見電話那端二娘哽咽的聲音。
最近,聽說年逾古稀的二伯和二娘正在辦簽證,要去美國投奔他們的兒子了,也不知以后能否再見到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