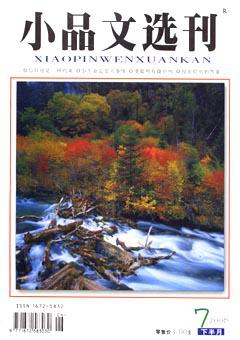不應該的疏忽
佚 名
我從小愛流鼻血,一家人為此很擔心,特別是父親。
曾聽父親說,我七歲那年,有一次流鼻血,家人想盡了一切辦法都無濟于事,最后竟到了昏迷的地步,他背著我連跑了十多公里的山路,我都毫無知覺。父親說:“那一次,可把我和你媽嚇壞了。”
五年前,身在異地求學,難耐酷暑的我鼻孔又一次血流不止。而恰巧生活費用完,為了求醫,我借了同學許多錢。迫不得已,決定開口向家里要。
那天,我正在寢室里給父親寫信,忽然鼻孔又出血了,有兩滴恰好滴在了信紙上、我用棉球塞住鼻孔,準備重新再寫。同室好友小海見了,說:“你快仰面躺下吧,那樣有利于止血。信,你口述,我幫你寫好了。”我囑咐小海說,把信紙上的血跡擦干凈,萬一弄不干凈,就另頁再寫。
過了一會兒,小海說:“好了,你接著剛才寫到的地方開始口述。”我以為小海已經把剛才寫的謄了下來,就開始口述。
由于第一次開口向家里要錢,又當著同學的面,所以,那封信七繞八彎地寫了很多。當小海將寫好的五大頁紙給我看時,我才發現第二頁上的血并沒有擦干凈;我不好意思再麻煩小海,就把它們裝入信封,讓同學幫我寄了。
不料十天后,一身塵土、汗流浹背的父親卻紅著雙眼站在了我的面前。原來父親接到信,發現了信上的血跡和兩種不同的筆體,以為我鼻血流得很厲害,到了“不得不請別人代寫信的地步”,所以就日夜兼程趕來了。
我一時不知該說什么好,要知道,從家到學校有兩千多公里的路程,要倒兩次汽車,坐兩天兩夜的火車。
父親見我已經沒事,放下五百多元錢,連口水也沒喝,就急著說要回家。我勸父親休息一晚再走,父親執意不肯,說:“你媽被你的信嚇個半死,還在家里等信兒呢。你沒事就好,再說家里正在收麥子,離不開人手啊!”
聽了一臉慈愛的父親毫無責怪之意的話,熱淚很快涌滿了眼眶,我暗暗責備自己為什么如此疏忽大意,害得正在農忙之中的家人為我著急。望著父親急急忙忙轉身漸漸遠去的已顯傴僂的背影,我只有在心里說:“對不起,爸爸,請原諒兒子本不應該的疏忽。”
選自《重慶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