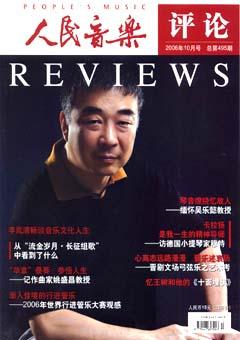交響音樂創作要更好地貼近群眾、貼近生活
2005年在全國音樂界隆重紀念反法西斯戰爭、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活動中,北京樂壇的傅庚辰和葉小綱的交響音樂作品音樂會使我受到一些啟發,即為了同一個目標完全可以寫出不同風格和創作個性的音樂。傅庚辰的交響音樂作品以作者過去所創作的聲樂作品為基礎,采取傳統的調性音樂創作技法;葉小綱則直接以樂隊的語言抒發他的感受,基本采用調性音樂與無調性音樂相結合的創作技法。他們的共同目標都是力圖創造出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盡量能為音樂聽眾所接受的、比較“雅俗共賞”的中國交響音樂。
中國交響音樂創作的真正起步是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左右,至今已有將近80年了。盡管當時在西方交響音樂的創作已經經歷了200多年,而且已進入了相當多元發展的階段,但在中國,它還只能以19世紀歐洲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音樂作為自己起步的樣板,一步步地向前摸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作曲家從起步階段就很清醒地想到要面向現實、面向聽眾、朝著民族化的方向做出自己的貢獻。完全照搬西方,從一開始就行不通。所以,80多年來,無論像黃自、江文也、冼星海、馬思聰、賀綠汀、丁善德等老一輩作曲家的作品,還是當時的中年作曲家瞿維、李煥之、羅忠镕、朱踐耳、陳培勛,以及當時的青年作曲家吳祖強、杜鳴心、施詠康、辛滬光、何占豪和陳鋼、王西麟、施萬春等,都不同程度地為中國交響音樂這一民族化的方向付出了自己寶貴的心血。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交響音樂的發展呈現出一種是以傳統技法和調性音樂為主、另一種是以大膽借鑒西方20世紀現代無調性技法為主的“新潮派”音樂。這兩種不同風格的作品,共同為中國交響音樂的發展作了更有力的推進。盡管開始人們對這兩種不同風格的交響音樂在認識上還存在分歧,甚至還出現了理論上的爭論,但是,中國的這兩種不同風格的交響音樂,都以擁有各自的聽眾而逐漸為社會所接受。因為,人們發現這兩種不同風格音樂作品之間并不存在什么原則性的對立。以傳統技法和調性音樂為主所創作的作品有它的長處,即大多旋律突出、和聲變化豐富鮮明、配器色彩對比清晰。這類交響音樂也不缺乏力度、節奏、色彩等方面的鮮明對比,但總的比較注重在復雜多變中求得平衡與和諧的美感,因而比較接近多數的音樂聽眾。而以現代音樂的理念和無調性技法為主的作品也有它的長處,即音色非常豐富、節奏的對比強烈,作者的個性突出,作品所包含的情感和意境更加復雜多變,而且它追求構建不同一般的新奇語境表達內心沖動。因而,它所體現的情趣往往與習慣于傳統音樂的聽眾還存在一定的距離。
如何使這兩種不同風格的交響音樂獲得更好的發展?我在此提出一些建議:
一,不可否認,無論中外,器樂創作是在聲樂創作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成熟的,在西方器樂創作的初期,這一情況是相當明顯的。從15世紀開始,尤其是所謂“巴洛克”的17—18世紀,曾經歷了許多摸索性的發展。當時,正值西方器樂創作的初創時期,他們常常運用以聲樂旋律給予變奏的處理(大多用于鍵盤樂器)或卡農、賦格式的復調模仿來解決(除了鍵盤樂器外還用于早期的樂隊創作,如亨德爾的《廣板》、巴赫的《詠嘆調》等)。也就是說,最初在西方器樂創作中帶有相當明顯的聲樂創作的影響。真正使西方器樂創作擺脫聲樂思維的束縛而不斷走向成熟是在18—19世紀之交的“維也納樂派”的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的創作中。他們將短小動機作動力性的展開,作為器樂樂思展開的基本手段,為古典主義的室內重奏和交響樂的創作發展奠定了基礎,從而真正推動了西方器樂創作的成熟發展。在中國也如此,在上個世紀30—40年代的不少器樂作品(如賀綠汀的《牧童短笛》《晚會》《森吉德瑪》,馬思聰的《思鄉曲》《牧歌》等)大多沒有真正脫離聲樂創作的影響。尤其是在一些作曲家力圖以民間音調為基礎探索器樂的民族化時,這個問題就更為突出。這種情形在50—60年代的一些創作中是很明顯的。在上個世紀60年代所展開的“交響音樂創作討論”就涉及了這一問題。直到今天,這個問題還不能說已經完全不存在。我們在創作聲樂作品方面的確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但如何將聲樂的思維改變為器樂的思維,特別是樂隊思維,應是進一步提高這類創作的一個關鍵。
我認為,應該善于將方整性的聲樂結構改變為以長短句的非方整性結構、或善于將樂節長的聲樂性旋律分解成若干短小的、更富于節奏特色的動機或主題,再根據作品的整體構思將這些富于個性的動機或主題給予各種藝術性的擴展,這是能否改變原來聲樂音調的關鍵。這不單純是創作的技術問題,而是涉及創作思維和創作觀念的問題。用民間音調和聲樂作品進行器樂性的改編,它可能在民族音調的多聲化、或對配器的運用上是一種好的鍛煉,但聲樂性的旋律常常會成為對器樂思維的一種束縛。特別是當運用聲樂性的旋律時,常常會有意無意地受歌詞敘述的影響,將器樂思維變成了“用器樂的語言來詮釋歌詞”。這個問題曾經是1961—1963年我國交響音樂創作討論的主要題目。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器樂作品都不能帶有歌唱性。過去在交響樂、室內樂作品中也有所謂“歌唱性的慢板樂章”,也能寫得很動情。但它的出現僅僅是大型套曲中的一個樂章、一個片段,而絕非是這部套曲的主體。這類創作如果以小品組曲的方式或許會更貼切。如江文也的《故都素描》、馬思聰的《山林之歌》、羅忠镕的《四川組曲》等。對一些形式稍大的作品,就有一個器樂性的創作處理問題。如劉鐵山、茅沅的《瑤族舞曲》、王義平的《貔貅舞曲》、李煥之的《春節序曲》、辛滬光的《嘎達梅林》、羅忠镕的《第一交響樂》以及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等,作曲家們或者利用配器變奏的方式來進行樂思的展開,或適當變動原來應用的聲樂主題給予音調的實質的展開、或加以結構性的處理,將歌曲性的主題適當給予動機化的處理(如《春節序曲》《第一交響樂》《嘎達梅林》《梁祝》協奏曲等。有的作品原有的曲調個性很強(如鋼琴協奏曲《黃河》、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作曲家也要善于在一些重點的段落能擺脫聲樂性的影響。有的作曲家雖然在主題的呈示時運用了原來民歌的主題,但又在這個主題的基礎上給予發展,并且還在樂思的展開中運用源于主題的短小動機來作為音樂展開的基礎。如馬思聰的《思鄉曲》、羅忠镕的《第一交響曲》等。辛滬光的《嘎達梅林》是源于內蒙古的同名民歌,但在作品的引子、主部、副部、展開部里,她都是從原民歌的旋律中分解或變化出新的動機或旋律來作為樂思擴展的基礎,而直到再現部之后的“慢板插部”中才全部呈現了原民歌主題。劉湲的一首作品,將冼星海的歌曲《在太行山上》干脆完整地放在最后樂章中出現,而在前面樂章都僅僅取其片段的音調(包括《酸棗刺》的音調)作為動機式的處理,我認為是比較好的。
二、對于較多借鑒西方現代無調性創作技法的“新潮式”的交響音樂創作,還是要關注更好地接近群眾的問題(首先是接近樂器演奏者),努力創造出更多為群眾喜歡的、“雅俗共賞”的樂隊作品。因為,一部音樂作品的優劣歸根結底必須由接受者來評定。行家可能有行家的標準,但是,作為對社會發生影響的藝術品的存在,作為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和社會承認的藝術創作,最終還要是由大多數聽眾來決定。尤其像交響音樂、歌劇等社會性較強的藝術品種,單靠少數行家的承認還是不夠的。這個道理本來是很簡單的,遺憾的是有一些理論家總是有意無意地抹殺這一點,總是置廣大音樂聽眾于不顧,過分強調發揮藝術家的個性并將其看作是衡量一部音樂創作是否屬于上乘的惟一標準。這對交響音樂創作的繁榮發展是不利的,尤其對年輕的作曲者更可能成為一種誤導。這在我國的音樂界、包括西方的嚴肅音樂界都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一個真正負有歷史使命的作曲家應該努力使自己的藝術創造緊貼時代和群眾的要求,而不是越來越脫離群眾,越來越走向孤僻、冷清,越來越將其社會影響讓位于通俗音樂,甚至那些格調低下的娛樂性流行音樂。我這樣說并非要貶低一切藝術的創新探索,但絕不能將單純的創新探索視為音樂創作的全部。
三、在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音樂藝術的過程中,我們進行藝術創新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認為是為了更好地創造出符合“雅俗共賞”美學原則的、符合“為人民服務”這一崇高目標的藝術。要真正做到藝術上的“雅俗共賞”其實并不簡單,歷史上大多數優秀的藝術遺產幾乎都是“雅俗共賞”的。有人說“雅”與“俗”是決然對立的、是無法“共賞”的。這個看法我覺得不符合中外文藝發展史的實際。希臘雕塑《維納斯》、意大利油畫《蒙娜麗莎》、中國小說《紅樓夢》等不朽的藝術精品就是為世人所公認的“雅俗共賞”的典型。中國昆曲逐漸走向衰落,中國古琴藝術越來越難以獲得新的突破,其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它們越來越陷于“雅”,越來越脫離“俗”的結果。金庸的小說之所以不同于一切的舊武俠小說,并獲得了各階層讀者的歡迎,侯寶林的相聲之所以為人們百聽不厭,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交響音樂之所以被稱為世界交響音樂的不朽名篇,絕不是因為它們的“俗而不雅”,絕不是它們缺乏高度的創作技巧。恰恰相反,正是他們做到了在自己藝術創造中體現“雅俗共賞”的藝術原則。如果我們承認藝術應該是時代的結晶,它的最終接受者是人民群眾,作為藝術創造者的作曲家就應該主動地去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而不是要求時代、生活、群眾來貼近自己。時代、生活、群眾是不會來貼近你的,只能期望它們的承認,否則就必將為它們所拋棄!
汪毓和 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專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于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