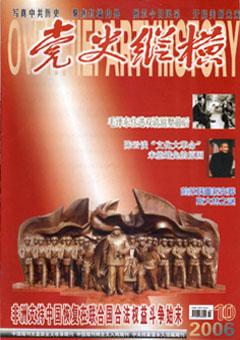淺議《監督法》的可操作性
田 春
備受矚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以下簡稱《監督法》)終于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以155票贊成,1票反對,5票棄權的高額票數獲得通過。作為一部憲法性法律,《監督法》條文的設立并沒有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上,而是具備了高度的可操作性。
《監督法》從1986年六屆全國人大開始醞釀起草,2002年8月九屆人大二十九次常委會初次審議,2004年8月十屆人大十一次常委會再次審議,2006年8月27日十屆人大二十三次常委會最后通過,前后經歷了長達20年的磨礪,這在我國立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其難點就在于監督法的政治性很強,涉及到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國家體制,監督權的行使涉及到人大與“一府兩院”的關系,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人大與“一府兩院”的關系既要有監督,又要有支持;既要依法監督,又不代行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怎樣在處理好這些關系的同時又能充分發揮人大監督的優勢?這就對《監督法》的可操作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值得欣喜的是,我們看到新頒布的《監督法》在這方面創造性地進行了大量細致縝密的規定。
首先,《監督法》實現了相關憲法性規定的具體化。《監督法》創設了各級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的專項工作報告制度,確立了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情況的執法檢查以及委托執法檢查制度,建立了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職權的公開制度等等。這些監督制度或監督方式并不完全是創新,在現行憲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組織法中,基本上都做出過相應的原則性規定,絕大多數也在過去的實踐中得到過不同程度的運用。遺憾的是,在《監督法》誕生之前,由于缺少配套的法律性監督程序,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導致某些制度和方式流于形式,并沒有真正發揮出其本應具備的監督功效,從而影響了人大監督的優勢。“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有效實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進行配合。現在,《監督法》將這些監督制度或監督方式歸納起來,以憲法性法律的高度進行了規范,明確了各級人大常委會各項監督活動的啟動條件、啟動機構或人員、相關問題處理的方式和時限以及最終處理,保證了各級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在重大問題和重大事項上的決定權。這些條文實際上是在現行的憲法以及有關的組織法的框架內,對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一府兩院”的制度,進行了具體化、程序化的規定。
其次,《監督法》從現實出發,符合當前國情。此次《監督法》從目前我國各級人大的工作體制現狀出發,符合當代中國的政治現實。例如,《監督法》既強調了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的專題工作報告,同時也規定:人大常委會要公布聽取和審議專題工作報告的年度計劃;正式聽取和審議專題工作報告之前,人大常委會的辦事機構還要將各方面對該項工作的意見匯總,交由被監督機構,以便讓被監督機構提前準備;“一府兩院”的專題工作報告在正式審議之前,還應提前20日送給人大常委會有關機構征求意見。從而給“一府兩院”修改自己的工作報告留下了更多的空間;人大常委會的審議意見交給被監督機構之后,被監督機構還應當將研究處理情況交給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機構征求意見,然后再向人大常委會提出書面報告,等等。這類細節性規定,在整部法律條文中隨處可見,充分顯示了立法者并不是僅僅停留在理念層面,而是表現出對當代政治現實的理解和尊重。通過這些技術性規范,無論是監督機構還是被監督機構,都將置于一個有章可循的監督過程之中。這樣既保障了《監督法》的可行性,同時也有助于提高監督過程的規范性、可預期性。另外,《監督法》還從實際出發,授權各省市人大常委會根據《監督法》和相關法律,結合本地具體情況制定實施辦法,這也是增強法律可操作性的一大舉措。
再次,《監督法》從實質上保障了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監督權。在現實生活中,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更多是規章以下的各種規范性文件,對于這些大量不屬于“法”的范疇的行為規范,往往因為審查虛置而出現違法亂治現象。比如一些權力機關為了地方或是個人利益而超越了法定權限或是違法發布決議、決定和命令,擅自設立審批、收費、罰款、處罰等等,嚴重損害老百姓合法利益,同時也阻礙了法治建設的順利發展。為此,監督法在“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專章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下一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作出的不適當決議、決定,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發布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這個稱得上“釜底抽薪”的硬性規定從本質上強化了各級人大行使監督權的力量,使其有能力及時清理、過濾掉違法的規范性文件,從源頭上保障法治的純潔和統一。
胡錦濤總書記在談到《監督法》的頒布時說:“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這句話可以說是言簡意賅,點到了問題的要害。再好的法律如果不具備可操作性,不能落到實處,都是一紙空文。毋庸諱言,《監督法》要想真正落到實處并沒有那么簡單,在具體施行過程中同樣會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有待我們去面對和克服。對于一些社會、公眾普遍關心關注的問題,比如,政府工作中的“三農”問題、教育問題、醫療改革、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社會保障等等;比如“兩院”工作當中的執行難、告狀難、賠償難、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司法不公等等,也不可能由于監督法的頒布就能在短時間內一一解決。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由于《監督法》突出了人大常委會監督的工作特點和優勢,注重監督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具備了很強的規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必將真正提高法治建設的力度,極大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