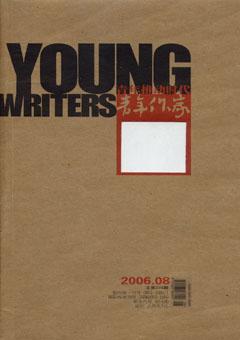會跑三步籃的姐姐
景鳳鳴
那天去省城的火車站,我送姐姐回縣城。是個陽光燦爛的夏日,風很涼爽宜人,閉上眼睛,有些秋日初晨的味道。
姐姐才從山東,那個據說和德國一個緯度的地方回來。背回來的東西留下了一些,又拿走了一些。還把以往的東西歸攏了一下,再拿走。
一些東西打在背包里,一些東西放在筐里。
筐是包裝帶編就的那種。這個城市不大用的,或者曾經用過如今被泛濫的塑料袋代替的。拎起來很占地方,也很扎眼。
姐姐說,放在這里也沒用,不如拿回去裝點啥。很樸素的想法。然后她就拎起那筐。爭了半天,才拿過來,由自己拎著,再和她共同拾那個包。姐姐走得有些慢,近半年腿似乎有些病痛。四十三歲的女人,總強調自己到了更年期,莫名其妙的心悸,心慌。不再關心自己的瘦身,別人問起身高時,總是往低了說,把一米六五的高度說成是一米六二五。總之不再是以前的那個風姿綽約的天生一副美妙歌喉并且會打籃球的姐姐了。
坐在清清爽爽的公交車上,我們姐弟倆就顯得刺眼。車里的紅男綠女們,都用簡潔明快的服裝,以及各式巧妙的挎包,表達著初夏的心情,用化過妝的、美容過的表情,表達生活的狀態。便想起以往和姐姐走在一起時,總是利索得令人矚目的。這次因為筐和提包,竟有不合時宜或者短了什么的意思。
終于走下公交車時,跟姐姐說了這個想法。姐姐說,那怕什么。誰不用這筐,這提兜。很振振有辭的。只是這樣說完,姐姐卻沉默起來。
姐姐沉默的時候,打量歲月給她留下的痕跡。姐姐的眼角和眼袋上已有了幾道很深的皺紋,表情平靜的時候也可以看得出的。這種皺紋如果笑起來,會很深重,或者沉重。牙齒略微地黃,面頰上有些血絲。聽信妹妹的盅惑,在小城風行紋眉與紋眼袋的時候,原來的兩道臥蠶眉拔成一道細線。這樣一個滿身清爽與淡色的季節,姐姐身著黑色的褲子,紅色的薄毛衣,頭發散亂或者蓬松著。未經過精心處理的那種蓬松。
這樣敘說姐姐的時候,姐姐似乎變得俗氣。事實上,姐姐坐在車廂里,或者背負著東西走在大街上,仍會引起男人女人的注意。除了姐姐清秀柔媚的氣質,還包含一種奇怪。這樣的女人,不應該是背負著行李在街上走的。
生活對于女人是什么?尤其一個事事要強的女人,一個站在女人堆里,立刻可以看到的女人,一個走在大街上,不經意的綽約姿態以及氣質,立刻引人重視的女人。姐姐那種孤傲與盛氣被湮沒了,骨子里不服輸沒有了。姐姐變成了一個有掙錢機會就想努力的女人,一個為讀高中的孩子如何考上大學和如何供念大學而心緒重重的女人。
后來去車站售票處。火車站正在修復,又一次莫名其妙的修復。需要過棧道,需要上樓。姐姐把筐和提兜留下來,不容分說地沖到人群中。姐姐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要自己買票,獨自承擔這份票錢。那個時候,姐姐的病痛沒有了,又恢復了原來的風風火火的狀態。沖到人群中的時候,似乎有三步籃的痕跡。三步籃是姐姐念初中的時候,摻到高中女子籃球隊練就的。雖有舞蹈的印象,卻不影響投籃的效果。人到籃下,手一壓腕,球已進筐。雖不是雄風糾糾的運動員,卻同樣呼嘯而來,勢不可擋。姐姐工作以后,參加教師球賽,姐姐的三步籃和投籃,很讓男同事們和女同事們驚奇。也是因為這一手,立刻被確定為女籃的核心球手。只是第一次比賽行,第二次比賽忽然不行了。姐姐那兩天得了腸炎。替換上場的是位中年女老師。那位老師很幽默,搶過球就跑,搶不到球就拉人衣角,充滿滑稽與幽默。全場因此哈哈地笑。觀眾席上的姐姐也快樂地大笑,笑得青春飛揚。那個時候,姐姐還是年輕的小媳婦。
站在站臺等姐姐。
三十八歲的弟弟,等四十三歲的姐姐出來。
陽光真的很明媚,盡管裝修隊切割大理石的聲音很刺耳,還有股股碎屑和煙塵。這個時空中,聚集容納著多少五行八作的人們,從搜求礦泉水瓶的拾荒者,到賣報的大學生,到生活雖有保障卻心路艱辛的姐姐,到高檔轎車一直送到豪華候車室的貴人。那時內心很慚愧,愿望卻很奢華,也很直接。想有個車,姐姐來的時候,能接或送一下。戴著白手套及墨鏡,穩穩地將車停在擁擠凌亂的廣場上,等姐姐款款下車,再到后備箱中拿出姐姐的行李背包。那種箱包式的,而不是條編筐。票自然要通過訂購方式,事先買好并且送達的。
天下的弟弟們都希望姐姐生活得滋潤。
后來姐姐出來了。她在男人的堆中,仍是幾乎平齊的身高。簡直搞不清她的一米六二五從何而來。只是票沒有買到,便和她去客運站。
姐姐不安地說,讓你跟著跑一早晨,不然能干很多事情的。到出站口,姐姐招呼住一輛價格便宜的貨用三輪車。我忙攔過一輛出租。這樣一個汽車城,出租車滿街流淌的地方,坐上慢悠悠的三輪車,耽誤事不說,要招人看一路的。姐姐又是抱歉地笑笑。那笑令人想起母親。想起這些年來,姐姐偷偷地對自己的關心,一時滿腹的無言。
姐姐坐長途汽車走的。我并未等到車發。工作時間有些緊,也不愿意站在車下呆呆地等著啟動。那樣彼此都不安定。我是帶著三十八歲應該有輛車的想法走的。接下來的工作,卻不是掙車買車的路跡或者軌道。我知道。
會跑三步籃的姐姐的身姿,隱褪了,隱褪了。現實的公交車中,拎筐的女人呈現出來,呈現出來。
責任編輯蔣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