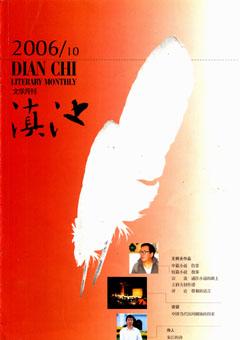帶刺的語言(評論)
冬天的豪豬在寒冷的驅使下每每會聚集在一起取暖,而周身的利刺又會讓它們無所適從,它們相互傷害,最后被落得個遍體鱗傷,流血奔逃。利刺是保護身軀用的,但卻有諸多無端的傷害。從某種意義上講,人也是帶刺的,這刺主要由語言構成,人與人之間的許多傷害也是由語言來執行的。
王祥夫的中篇小說《傷害》也就是敘述了這樣一場由語言所執行的傷害,這是一場家庭風波,是一場有誤會的罵架斗氣,大致上屬于家庭問題。也經歷了由導火線到點燃到擴大化再到一發不可收拾最后真相大白的過程,小說一來就談肝火和脾氣都很旺盛的董老師把家里具有象征意義的雙人大床給鋸開了,緊跟而上的就是開戰,整個小說的精華集中在人物的語言對白上,語言的力度在這場斗氣中不經意地就體現出來,話語在人物之間呈現出直線運動,就像子彈一樣直線出擊。少了拋物線這樣一個優美的迂回的弧線運動過程,語言在斗氣中很有質地,加上怒氣與肝火,就變得有硬度并且冷漠。傷害由此而展開,斗氣的結果卻是一個誤會,一張不準確的驗血單跟這一家子三口人開了一個玩笑。戰斗在董老師一聲憤怒的“不——”的嚎叫聲中戛然而止,可以說表面上整個風波來的突然,去的也飛快,其實在深層卻涉及到了家庭問題,涉及到了語言的深層問題,于是。這傷害就像是幾個人歇斯底里后的余音,久久盤亙不去。
《傷害》中的傷害是硬直話語造成的傷害,這里面沒有太多的來自于道德的或是外界社會的傷害,沒有皮肉之苦,也沒有來自于法律的強制性,而更多的是缺少交流的基礎上的一種話語挫傷。必要的溝通是需要的無論是一個家庭還是整個社會。難怪有人說,很多戰爭是由于語言隔閡而引起。整個小說除了平淡的、不溫不火的敘述性文字之外,那就是人物之間的質問和吼叫。里面敘述性的文字多少有點像戲劇中的旁白,時不時還插入一些插科打諢性的輕松的話語,但一家三口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卻不斷地上升,這種沖突與矛盾在小說中整個表現為董老師與妻子燒餅及其女兒董笑的交鋒上。因而整篇小說就像一出戲劇在上演,而對話所使用的則是典型的“直腸子”式的話語,不拐彎抹角,這是一種純質樸的不含修辭的話語,有著粗俗的棱角,外加一點火藥味,于是便直擊對方的心坎,它雖說比不上魯迅的那種含沙射影反諷式的“投槍匕首”,沒有那種深刻的底蘊,但也像鈍刀砍人,有一種疼的味道。從一開始燒餅的出場就來一連串的發問:“董文明你要做什么?……啊呀!……干什么?……啊!干什么!”咄咄逼人,直指對方。一直到結尾,每個音符都像是高音喇叭所發出,大多是尖叫和吼叫,話語構成了傷害的內容。他們似乎在發泄,但卻沒有發現正在傷害著。人物的對話語言脫口而出,在那樣的境況之下沒有思考的時間,更別說是潤色的機會,罵架時的語境似乎更有利于這種直露的、質樸的語言出場,慎言的言語教條失去了作用,《傷害》的精髓也正是在于回到了人物最本原最質樸的語言本色。
董老師叫董文明,其實也無多少文明可言,他的言辭既不溫柔可人也不委婉含蓄,可以說他是一個“壯棒”,他鋸床分家,似乎表示了一種決裂,他火氣十足,不留余地。如“上來!…”“把她個燒餅!”“讓她們遠遠地滾!”“讓她們睡狗窩去!”語氣強烈,語調生硬,他或許是自尊心受到了打擊,很是窩火,想發泄點什么,也想找回點什么,單他什么也沒有得到,只有傷害而已,傷害就是被傷害,語言要指向外在的人或物,但語言是雙面刃,如同炮膛里的火藥一樣火力太足也會炸毀炮膛。
燒餅是董老師的老婆,因做燒餅而得名,“燒餅”一詞是董老師的硬傷,燒餅的話外音是人人得而吃之,我個人猜想董老師一定討厭吃燒餅,當董老師聽到幾個小女孩一齊發喊“小燒餅,五毛錢一個小燒餅——”時反應強烈,他一肚子悶氣,很想打人。燒餅一家明顯表現出一種語言上的隔膜,他們的家庭問題是缺少最起碼的感情交流,更談不上理解,憑一字之據就貿然行動,可以說是平時的諸多的摩擦的總爆發,一紙化驗單僅只是個導火線,在董老師的內心深處也不是要離婚,從他語言的火藥味十足和情感與話語的矛盾上看,他僅只是想發動一場爭斗,只想在這場爭斗中找回作為男人的自尊,他也在與自己作斗爭,死要面子活受罪,在內心深處希望老母親能平息這場爭斗,他自己的所謂的言不由衷使事情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他的話語與情感表現出分裂,這是一種不自覺,這些不自覺的話語主要由氣和憤怒構成,他的話語沒有經過潤色,直線式的直接指向對方,他本想讓燒餅和董笑進屋,理智和情感都是這樣,但就是說不出口,一說出來就走了樣,“讓她們遠遠的滾!”這是不和諧的音符,其實董老師還是很在乎,所以有情感的一面,傷害總是有感情的傷害,質樸的情感同樣被話語的悶棍擊打得七零八落。為什么“你們都進來吧”這樣的話就是說不出口呢?這一點似乎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董老師火氣不是那么足,如果話語轉個彎,有個回旋的余地,那么就會是另一篇小說。因此在這篇小說中是話語構成了傷害。董老師口硬心軟,心口不一,這是令人惱火的,他就那么在乎,在乎純潔,在乎得單純和愚直。離婚在今天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和難事,冷冰冰的法律一紙文書就可以宣判婚姻的無效。然而傷害中又不全是這種冷色調,董老師要做的仿佛是“中國式的休妻”。在中國古代,如果妻子“行為不端,舉止失當”,按慣例是要被一紙休書遣送回娘家的。董老師的做法好像是介于二者之間。超越了家丑不可外揚的階段,但也沒有達到付諸于法律的階段。
在小說《傷害》中,董笑的話語又是最突出的,無論是在與其父親還是母親對話,十五歲的董笑都是那么的異常,董笑本來應該是“懂笑”的,但她卻只有哭的份了。笑笑的這種表現在《傷害》中極不協調。她的話語對白很少,集中在三處。先是董老師突然很機械的習慣性叫:“笑笑上車!”董笑忽然就大哭起來,并且以極尖銳的聲音叫到:“不上!不上!不上!”“上來!”“不上!不上!不上!”“上來!…”“不上!不上!不上!”笑笑叫得更尖厲,哭的更厲害。“你上不上?”“就不上——”笑笑的聲音拖得很長而且十分尖厲,“像是已經劃過小鎮的整個天空,天空上好像已經有劃痕了。”作者這樣描寫到。其次是和她母親去找劉再進的時候,“你去不去”,“不去!”“不去也得去。”“不去——”“你還叫,你去不去!”“不去——”完完全全的尖叫。最后就是小說的結尾部分,“咱們回家吧!”“不——”“咱們回家,回家!”“不——”……“吃飯吧?”“不——”這三處對話,命令與反抗,質問與否定,用話語把傷害推向高潮,對于語言的傷害,最直接的對抗就是否定,董笑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傷害被語言演繹得淋漓盡致。“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話語是最好的良藥,能撫慰最通徹肺腑的傷痛,同時也是最有殺傷力的武器,而小說《傷害》中就體現了語言的最直接的傷害,最痛的傷害。
小說《傷害》傷害的核心在于斗氣時的語言所體現出來的傷害性,整個小說的語言都顯示了質樸和俚俗的力度,直白的話語,尖銳的對白,顯得冷漠和僵硬。可以說是一種異樣的聲音,是一種不和諧的對話,不和諧就難免有磕磕碰碰,難免有傷害。我出生在農村,總覺得農村缺少足夠的交流,就像兩塊璞玉放在一起,不能交相輝映,很多的對話是嚴肅的教條式的。夫婦之間、父子之間、兄弟之間,直接的指責、指使、詰問更能表達出這種直白的語言風格。小說《傷害》中的尖銳對話與不和諧恰恰就反映了這些特征。小說的最后作者顯然是玩了一個小技巧,也想其短篇小說《找事》那樣出人意外,來得很真實,去時卻有些莫名其妙,作者還是希望這種傷害能夠得到結束,希望這樣的家庭一團和氣。但我卻覺得,語言的發生來自語境,語言的特質與他所產生的環境有斬不斷的關系,環境不變,傷害仍然會繼續。
(吳遠穩云南大學在校研究生)
本欄責任編輯雷平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