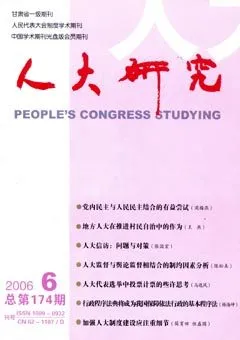禁止“網絡語匯”凸顯地方立法六大缺陷
2005年12月29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上海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該辦法于2006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該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漢語文出版物、國家機關公文應當符合國家關于普通話、規范漢字、漢語拼音、標點符號、數字用法等的規范和標準。國家機關公文、教科書不得使用不符合現代漢語詞匯和語法規范的網絡語匯。新聞報道除需要外,不得使用不符合現代漢語詞匯和語法規范的網絡語匯。”除上海市外,我國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配套立法中,均未出現對“網絡語匯”的禁止性規定,上海市的這一規定,確有“標新立異”之處。由于對目前已經在人們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的一些網絡詞匯的使用進行了限制,該條規定非常引人注目,也招來不少的批評與反對。有人以激烈的言辭指出,這種規定是19世紀的語言“規定主義”、“純語主義”在中國大都市的“陰魂不散”[1]。而筆者則認為,這個條款無非是一個縮影,其背后表現著我國目前地方立法中存在的諸多缺陷。
一、在執行性立法中隨意加入創制性條款
作為國家標準,《漢語信息處理詞匯01部分:基本術語》分別對語言、文字、詞、詞匯等給出定義。語言是指為了傳遞信息而使用的一組字符、約定和規則。文字是指人類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詞是指最小能獨立運用的語言單位。詞匯是指一種語言中所有的詞和固定詞組的集合。漢字是指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
《辦法》中的“語匯”一詞,按照《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指“一種語言的或一個人所用的詞和固定的詞組的總和”。可見,“語匯”實質上就是詞和詞組,它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中使用的“文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詞可以由一個字組成,也可以由幾個字組成。“字”≠“詞”,這個道理應該是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的。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條明確規定:“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范漢字。”其立法作用是推廣普通話,推行規范漢字。很明顯,該法規定只針對字,而不針對詞;只推行規范漢字,而不推行“規范漢語詞匯”,其范圍和界限是十分明確的。
從標題以及《辦法》第一條的規定來看,《辦法》屬于執行性立法。執行性立法必須將其內容嚴格地限定在它所要執行的法律的內容之中,而不得設定新的權利、義務規范。但是,《辦法》對于網絡語匯使用的禁止超出了《辦法》所要實施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范圍,其性質是在執行性立法中出現的創制性立法條款。這是違反一般的立法原則的。
二、對非地方性事務進行創制性立法
假如該條款并不是處于一部執行性立法,單就該條款的內容而言,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是否有權就此事項進行創制性立法呢?
根據《立法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地方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只能就“屬于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進行創制性立法。也就是說,地方進行創制性立法,只能針對“地方性事務”。那么,國家機關公文、教科書和新聞報道使用的語言文字,是否屬于地方性事務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原因是語言文字使用的主體無法被限定在地方范圍之內。國家機關公文的制作主體是各級國家機關,在上海市范圍內使用的國家機關公文包括中央國家機關和其他地方國家機關的公文,上海市各級國家機關只是這些國家機關中的一部分。這里面不僅包括在上海市以外的各級各類國家機關制作的公文,在上海市范圍內可以被使用;還包括在上海市內一些屬于中央直接管轄的國家機關制作的公文。教科書和新聞報道同樣如此。這個法規是否可以針對在上海市的駐軍制作的公文?是否可以針對法律出版社制作的教科書?是否可以針對中央電視臺播放的新聞報道?
三、立法用詞含義模糊
“網絡語匯”一詞中,最令人難以捉摸的就是“網絡”二字。“網絡語匯”究竟是指被網絡使用的語匯?還是指起源于網絡的語匯?事實上,無論持哪一種理解,這個概念都是很難準確定義的。
由于目前網絡已經非常發達,網絡的使用也極為頻繁,網絡已構成了人們生活的一個虛擬世界。可以推斷,所有的漢語詞匯都在網絡中被使用和發布。如果認為“網絡語匯”是指被網絡使用的語匯,那么幾乎所有的漢語詞匯都應被認定為網絡詞匯。很顯然,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絕不可能想去禁止使用全部漢語詞匯。他們所想禁止的是那種“不符合現代漢語詞匯和語法規范”的詞匯而已。假如是這個意思,那么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就根本無需使用“網絡語匯”一詞,將“網絡”二字去掉,仍能準確反映其立法原意。而在立法中出現“網絡”二字,除了使立法用詞含義模糊之外,更反映出立法者對網絡的“歧視”或者“恐懼”。
將“網絡語匯”理解成源自于網絡的語匯,同樣難以進行判斷。究竟由誰,在何時創造了某個詞匯,這個確認工作是相當困難的。在有關“網絡語匯”的宣傳報道中,“美眉”、“恐龍”、“PK”之類的詞,似乎被“確定”為“網絡語匯”的代表,但實際上,這種“確定”充其量只能被稱為“假定”、“推定”。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在立法的時候有沒有經過調查,舉出證據來說,這些詞匯就是源于網絡呢?
四、立法出現禁止性規定,但不事先公布判斷標準
立法中的禁止性規定,構成人們的不作為義務。假如該禁止事項的用語按照語言規則,無法被非常準確地界定,容易產生歧義的話,人們將無法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準確預期。因此,如果立法中包含對某種行為的禁止,立法機關就有義務在立法中或者授權某個國家機關在法律生效以前或同時提供該種行為的判斷標準。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相配套,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等有關部門就頒布了一系列國家標準。但是,這些標準中并不包括有關“語匯”的標準。上海市人大常委會至今也未頒布地方標準來界定“網絡語匯”。在此狀態下,執法權力將是恣意的,因為執法機關可以對“網絡語匯”進行任意的擴張性解釋。
五、立法不認真對待民意
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這是立法法所規定的基本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是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本身就是民意的代表機構。同時,地方人大進行立法時,可以參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程序的有關規定廣泛地搜集民意。《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規條例》也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地方性法規案,法制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區(縣)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其他有關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對于設置普遍性禁止的事項,尤其應充分地、認真地聽取人民的意見。從各類媒體的評論來看,對禁止“網絡語匯”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就評論的內容來看,反對觀點措辭激烈強硬,顯示出強烈的“偏好”。既然尚存在如此廣泛和強烈的反對意見,為什么還要強行立法?
六、立法不考慮可操作性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之所以不對詞匯設定國家標準是合理的。國家可以為符號設定統一的標準,幫助人們認字,方便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傳播。但人們如何理解這些符號的組合卻屬于純粹思想領域的事項,國家既不可能全面了解,也根本無法強制。人們可以在生活實踐中創造新詞;也可以為已有詞匯賦予新的含義。語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具有極強的變動性,任何政府和組織都沒有能力去左右語言的發展。正因為如此,禁止“網絡語匯”,實際上就是要政府去辦它所辦不到的事情。
同時,由于前面提到的用語定義模糊的原因,執法者在具體操作時也將面臨困境。究竟哪些是“網絡語匯”?立法者既沒有告訴人民,也沒有告訴執法者。是不是要參照詞典來操作呢?哪本詞典才是“權威”詞典呢?
注釋:
[1]見《誰有權利禁止語言?——評兩篇有關上海語言文字地方立法的報道》一文,見上海語言文字網論壇。
(作者系蘇州大學法學院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