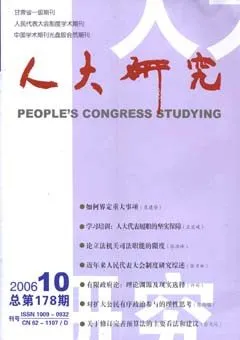建立“人大代表辭職制度”質疑
自1999年湖北省襄陽市試行“人大代表辭職制度”以后,浙江寧波、湖南溆浦、江蘇常州、福建晉江、山東即墨、成都金牛等許多地方紛紛效法,一時“人大代表辭職制度”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對此,許多新聞工作者、法律工作者、人大工作者發表了各自的看法,褒貶不一。
關于“人大代表辭職制度”的依據問題
根據現行法律,人大代表辭職是有法律依據的。《選舉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辭職,鄉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書面提出辭職。”但是,根據筆者的理解,法律意義上的“辭職”和襄陽、寧波等地試行的“人大代表辭職制度”不是一回事。法律意義上的“辭職”,很顯然是人大代表的一種自愿行為,主動行為,不帶任何的勉強,不受第三者的支配或勸說,不受外來壓力的干擾。而襄陽、寧波等地試行的“人大代表辭職制度”,先由人大常委會人事代表工委根據代表變動情況,提出需要辭職的代表名單,提交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討論,然后向同級黨委報告,經同級黨委同意,才由組織出面向人大代表提出辭職建議,建議時還輔以思想政治工作,最后由代表根據組織要求提交辭呈。最近江蘇省灌南縣則公開采用“勸辭”的辦法辭退了20名人大代表。所以,這種做法看似代表自愿,實際是由組織決定的。有自愿之形,而無自愿之實。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凡是接到組織辭職“建議”的人大代表,沒有一個不接受的,包括灌南縣某鄉鄉長雖心有不愿,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露了不情愿,然行動上還是“服從”了。這種做法,與其說是“辭職”,還不如說是“辭退”。而“辭退”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因此,襄陽、寧波、灌南等地的“人大代表辭職制度”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起碼是法律依據不充分。一位自認為“被迫” 辭職的代表也說:建議代表辭職,有“強人所難和逾越法律之嫌”。
建立“人大代表辭職制度”要解決的問題
寧波市寧海縣人大常委會人事代表工委主任張萍說:人大代表辭職制度“是一個被逼出來的制度”。這一個“逼”字,足以說明這個制度要解決的問題之多、之嚴重!灌南縣則講得比較直接具體,是為了解決“代表調入縣城引發的困局”(《人民代表報》2006年4月20日第一版《聚集灌南20名人大代表辭職》)。概括各地的情況,大致要解決以下問題。
(一)不便履職問題。認為較多的人大代表調離原選區以后,很難參加原選區的代表活動,不利于聯系原選區的選民,不利于有效地履行人大代表的職務,也不利于接受原選區選民的監督。
(二)配置不均問題。人大代表作為一種民主的資源,按照法律規定,要根據選區的人口數相對均勻配置。這一方面有利于一方選民的意愿的正確表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上級根據代表的建議正確決策。代表屆內變動,打破了選舉時名額的均勻配置,需要調整,保持均衡。
(三)工作需要問題。縣市人代會期間,代表團團長一般由鄉鎮黨委、人大或政府主要負責人擔任。這些“官員代表”調離后,無合適人選擔任團長,影響了會議期間人大代表工作的開展;閉會期間,缺少了這些“官員代表”,也便缺少了骨干,缺少了物質和經費的保障,正常的代表活動也難開展,即使開展了,活動質量也大打折扣。所以根據工作需要,該辭的要辭,該補的要補。
(四)能進能出的問題。成都市金牛區人大常委會的同志說,實行辭職制度的另一個原因是,過去人大代表實行“終屆制”,讓代表缺少緊迫感、使命感,認為只要不違法、犯罪,即使不參加會議、不參加活動、不履行職責,任期也會直到屆滿。
誠然,以上問題在各地或多或少、或輕或重地存在著。但是,筆者認為,實行所謂的“人大代表辭職制度”,不僅不是用正確的方法解決問題,而且也不可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關于方法不正確,前已闡明,是因為這一“制度”有違法律精神。講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是說這一“制度”試行以后,問題仍然存在。如履職問題,不便履職不等于不能履職;有心履職,即使人事關系調離,但仍然心系選區,可以積極履職;無心履職,即使人在,也可能對選民的意愿、呼聲仍然置若罔聞,起不到任何作用。不會因這一“制度”而有所改善。如配置不均問題,僅是對干部無序調動、無度調動的一種被動應付。按理,組織部門在換屆之初就應慎重考慮,屆內要相對穩定,即使變動也屬個別,但許多地方不到一年,就有較多人事變動,到兩年、三年,鄉鎮主要領導變動已經過半,一面調,一面辭,一面補,永遠沒有配置均衡之日。即使勉強保持動態平衡,于黨政班子建設、人大代表隊伍建設又有何益!至于為解決工作需要問題服“辭職制度”這帖藥,只能反映我們人大代表身份的依附性,只能反映法律規定的人大代表開展工作的保障沒有落到實處。最后關于能進能出問題,這在《代表法》里已經有明確規定,“辭職制度”似屬“蛇足”。
建立“人大代表辭職制度”反映出的一些問題
“人大代表辭職制度”,實屬一個不該建立的制度,它像所有不合法、不科學的制度設計一樣,不但有違設計者的初衷,而且帶來了一些問題。
(一)有違民意問題。“人大代表人民選,人大代表為人民”這一共識,不僅浸潤著先進的民主選舉文化,也是對《憲法》《組織法》《選舉YxBEOe5Yko1DLKrhcJQLSQ==法》《代表法》關于人大代表產生和職責等法律條款的樸實詮釋,隨著民主政治的進步,已深入人心。直白地講,選民,也只有選民,才能決定人大代表的去留!人大常委會人事代表工作委員會是人大代表開展工作的服務機構,無權提出人大代表辭職建議名單,黨委組織部作為黨委的工作部門,只有組織人民當家作主的義務,也無權對人大代表辭職建議名單進行研究并作出決定,因而“人大代表辭職制度”,從設計到實踐,都不適當。
(二)違背法律問題。人大代表是選民依法選舉產生的,依法選舉產生以后,他們的地位是法律賦予的,不是本人意愿,就不能用組織的名義和壓力動員其辭職。至于對“建議”以后仍不愿辭去代表職務的人員就地免職,或者不予調動升遷,就更違法理。因而,建立“人大代表辭職制度”不僅沒有法律依據,而且與現行法律抵觸。
(三)職務隨意性問題。法律規定,人大代表是一種職務,是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但是“人大代表辭職制度”不是因為代表有違法犯罪或其他嚴重錯誤而被罷免或終止,卻是因為鄉鎮黨委書記、鎮長、人大主席等職務的變動而被“建議” 辭職。這表明了人大代表職務的依附性,先因“工作需要”要你當,后因“工作需要”請你辭,顯得隨意,不嚴肅。
(四)物質保障問題。《代表法》第四章規定了代表執行職務的時間保障、誤工待遇以及活動經費列支渠道。而“人大代表辭職制度”暴露了這些法律條款在許多地方沒有貫徹落到實處,隨著一些“官員代表”的調離,經費、車輛、場所等物質保障就無法解決。
(五)無序調干問題。換屆前夕,上級組織部門應該根據工作需要,在嚴格考察、廣泛征求多方意見的基礎上,根據結構優化的原則,對各套班子審慎考慮、統籌安排,增強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學性。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往往是一個地方特別是鄉鎮的黨政主要領導在一個地方干了一兩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就由于種種原因,予以調動,隨意性較大,連“屆”的概念也沒有。這樣的后果不僅會使某些代表履職困難,同時,也使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作為權力機關的人大,應該有責任對這種現象說“不”,應從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加強工作監督和法律監督的角度,向有關部門諫言干部無序調的嚴重弊端,以緩解和阻止這種不正常現象的頻繁發生。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人大代表辭職問題應按《組織法》《代表法》《選舉法》 中的有關規定規范解決。“人大代表辭職制度”作為一種“制度”的建立和推行應該慎之又慎,三思而行,不應為解決一時的難題而“硬性”推行,更不能作為一種時髦而盲目仿效。
(作者單位:江蘇省啟東市人大常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