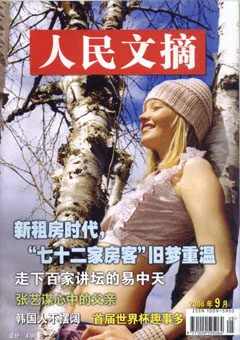走進印鈔女孩的絕密生活
中國是世界上鈔票流量最大的國家,也是印鈔大國。對于頗顯神秘的印鈔人,我們充滿好奇:每天面對花花綠綠的鈔票,他們真能毫不動心嗎?印鈔員每月能掙多少錢?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不同尋常之處?
人民幣“出爐”內幕
2006年3月的一天,陽光很好,記者如約在北京印鈔廠附近一家西餐廳見到了王倩——一個開朗活潑、氣質干凈的28歲女孩。
王倩的父親是寧夏人,從北京退伍后分配到印鈔廠工作,并在京城安家。如今,王倩一家四口都是北京印鈔廠的職工,父母是雕版師,她是檢封員,大學剛畢業的妹妹在廠里當秘書。從1997年中專畢業后進廠算起,王倩已經整整印了9年人民幣,但許多親友至今仍以為她在普通的印刷廠工作!
王倩進入印鈔廠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保密條例:不許到車間別的班組串門,不許向朋友說自己在印鈔廠工作,不許跟人談論關于鈔票印刷的事情……
一張人民幣,從手工雕刻模板到印刷出廠,至少要經過十多道工序。初進廠時,王倩是一名選紙工。人民幣生產的第一個環節就是選紙,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質檢了,它被稱為印鈔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剛被調到檢封大廳工作時,王倩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這里特像大學圖書館的閱覽室:一個個半封閉似的工作臺整齊排列著,一個個質檢女工的手里和桌上是一沓沓新版人民幣。明亮的燈光水銀般傾瀉著,每個桌上還亮著一盞高瓦數的臺燈。燈光對她們很重要,因為要在燈光下檢驗每一張人民幣的質量,比如號碼和文字有沒有印錯,顏色是否均勻,水印有沒有倒置,等等,然后剔除廢票。記者禁不住問王倩:“你一天要檢查多少張人民幣?”她回答說:“幾萬張。”
別以為每天經手大把鈔票的感覺很過癮,其實,王倩的工作是十分單調和辛苦的。試想每小時、每天、每月、每年都是盯著同一種畫面反復檢驗,有多少年輕人能耐得住這份枯燥乏味呢?在印鈔廠上班的第5年,王倩的眼睛就開始出現異樣,時常感到酸澀、疲倦,并會莫名其妙地流眼淚。年輕愛美的她最喜歡自己那秋波流轉的大眼睛,如今這雙美目卻在工作中累出了毛病。而她的幾位女同事才30多歲就花了眼,只能戴著眼鏡工作。
經王倩她們質檢合格的“產品”,點清數目之后被封裝進一個個木箱中,然后送到中國人民銀行的“國庫”里。女孩說,只有經央行發放出去,這些“產品”才可以被稱作“錢”。
視成捆鈔票如“白菜”
王倩打趣說,她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工,因為每天經手的鈔票都有幾百上千萬!而且,她還負責管理一個大得驚人的錢柜,她們整個質檢組的合格產品,都放在這個錢柜里。“但實際上我又是個標準的窮人,月薪只有1000多元。”
在印鈔廠工作,雖然滿眼看見的都是鈔票,但生產數量有嚴格的控制,就連有瑕疵的人民幣也不能隨意扔掉,必須上交,每隔一段時間上面還要核對,一旦查出問題,“整個部門的人都要接受調查”。此外,全廠每個車間都安裝了24小時不停歇的攝像系統,任何時間、任何部門發生的事,都可以從電腦記錄中調出來查閱。
當問到王倩面對花花綠綠的鈔票,是否也會有怦然心動的時刻時,女孩嚴肅地說:“這些成捆成堆的人民幣在我的眼中不是錢,它們就像其它行業工人手中的產品一樣,甚至像農民看著地里的大白菜、西紅柿。我不能把手中的這些錢跟商場中的商品聯系起來,我心里只有一個想法:干好活,不出錯。”的確印鈔業是一個具有獨特企業文化的行業,管理者會反復向工人們灌輸這樣一種思想:“你面對的是產品,不是錢。”
談及印鈔廠“嚴”字當頭的管理制度,王倩講述了去年發生的一場“事故”。2005年7月,某生產車間發現兩張100元的人民幣產品各缺了一個角,這兩個錢角立即引起了上至總公司下至全廠職工的高度重視。可是,個把月下來,依然沒有定論。但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兩個缺掉的“角”需要領導來“補償”。按理說,出了兩張缺角100元人民幣次品,按1:1扣發領導200元工資已經夠嚴格了,可結果卻是:廠領導被扣一年綜合考核獎等獎金上萬元,處領導被扣數千元,該車間的工人被全體“記過”一次!
“業內的人都知道,世界上鈔票防偽技術最先進的是瑞士法郎,可以說瑞郎集世界先進防偽技術之大成,但技術含量高,成本也高。據測算,一張1000元瑞士法郎的生產成本需3~4元人民幣。我國第五套人民幣的防偽技術就是以瑞士法郎為樣板,但我們的生產成本卻低多了。幾位中國設計師的杰作,令瑞士同行都感到吃驚!”當問起我國生產一張百元人民幣的成本是多少時,儼然已是“半個專家”的王倩卻詭秘一笑,避開不談,只說“這是秘密”。
人民幣是一種特殊產品,它的質量關系到國家的名譽。正因有了王倩這些印鈔人的辛勞付出,被稱為“國家名片”的人民幣,才能以卓爾不群的身姿出現在世人面前。
一位老作家曾為北京印鈔廠工人寫下這樣的贊詞:“錢積如山,德立干仞;錢流如川,心如止水。”這16個字反映的不只是北京印鈔廠,更是中國印鈔人高度的職業道德和精神境界!
(朱虹摘自《北京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