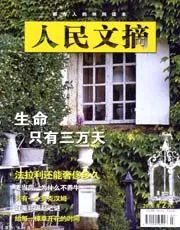陸川:可可西里的眼睛
生于70年代初的陸川無疑是現時中國最年輕的導演,從1998年開始,他就已經嘗試用沉默和努力尋求自己的未來,他用5年的時間證明了自己。在《可可西里》上映的今天,他依舊保持沉默。那些受過的苦流過的淚都埋在心里,他不想讓人知道過程,影片才是有資格說話的惟一途徑。
把生命中最激情的部分留給電影
陸川的那位著名作家父親在一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的稱謂已經在不覺中改變,“陸川的父親”,別人如此稱呼他。父親來不及高興,趕緊把陸川叫來,給了他一句又紅又專的話:懂得做人。
兩年后的今天再次說起以上這幕,陸川的語氣輕松,但在這看似輕松的背后,卻仍然蘊藏著無限的感激與領悟。“我很慶幸自己是個正常的孩子。”在該讀大學的時候讀大學,在該憤青的時候憤青,在該戀愛的時候頂著天大的壓力戀愛。他慶幸自己的聰明沒有在小時候就暴露無遺,而是在以后的歲月里一點點地揮發……
外表儒雅的陸川,從緊閉的嘴角露出些許固執,只有他在說話的時候,固執才稍稍地撬開一個角,流露出更多的隨和。
他快樂地說:“要把生命中最激情的部分留給電影。在十五六年中,我慢慢積累每一個能靠近電影的機會。”“從89年開始,我每星期三、四、五都看電影,有時候在禮堂,有時候在操場,幾乎全這樣。慢慢地,你就會感覺雖然電影是你的夢想,但你被生活沖得越來越遠,跟電影一點兒關系都沒有,那種感覺挺難受的。就像我喜歡一個女孩,但是眼見她越走越遠,最后嫁人了,看著她親昵地挽著別人的手,那個時候就是這樣。”
80年代,正在上中學的陸川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被《紅高粱》擊中,剎那間五雷轟頂的一種感受,原來一部電影可以如此表達。文學在它的面前,如一個弱不禁風的小孩面對一個強壯的男人。電影可以徹底地粉碎一個人。
記不得那是一個什么樣的日子
偶爾經過北京電影學院的陸川看見了一則招生啟事。于是命運從這個時候轉了方向。其實這樣的一種結局遲早是會發生的,只是,命運偏偏讓這個結局在這樣一個時刻到來了。
電影學院研究生畢業后,兩年內他沒有任何收入。他像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寫劇本,找劇本。還好,兩年后,他等來了《尋槍》。
“《尋槍》的本子寫得很順利,我也不否認它帶給我的滿足。第一稿寫得很沖動,大概10天就寫完了,把自己感動得涕淚橫流,基本上打幾個字要擦一下眼淚,完全是一個徹底狂熱燒包的狀態。”
然而等待卻是一種最大最痛的煎熬,難以用語言形容《尋槍》之于陸川的意義,他是用一種類似宗教的虔誠來對待這部處女作的:改了一稿,又是一稿,又要拿去給別人看了……
整整一年多的時間,兩條路不停地交錯在他面前:一條是通往深遠的道路,能夠暫時令他欣喜;而另一方面,他感覺自己仿佛是塵封在禮盒里的老式糕點,在墻角里慢慢地發霉長毛。但無論怎樣,電影還是要拍,劇本還是要寫,飯還是要吃。至今他都清楚地記得那一天,言辭灼灼地對凡一平說:“我是一個年輕導演,沒有什么資歷。可是我非常喜歡《尋槍記》,它里面有意義。如果你相信我,我一定會讓所有的人知道這部小說的意義。”
我一直覺得我要死了
2003年11月28日,《可可西里》在青海湖關機。但是這并不是一個句號。陸川又馬不停蹄地開始后期剪輯,包括馬不停蹄地宣傳。
“在可可西里,我的伙伴們配合我完成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感謝他們,在那么艱苦的情況下沒有退縮。”7天的時間,他們穿過了可可西里。“我們什么都看到了,成群的藏羚羊、狼、熊、沙狐,體會到絕境中人與人最真的情感,也嘗到了肉體從未有過的痛苦,海拔6200米的高原,走到最后我都覺得自己快要死了,是那些尋山隊員給我以力量。”
真正讓他感到生死無常的,是葛路明的罹難。和陸川幾乎同齡的美國人葛路明在前往《可可西里》探班途中,不幸遭遇車禍。看著曾經有說有笑的同事轉眼離自己那么遠,陸川痛哭不已。他不能僅僅用內疚來形容自己的心情,而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人生為什么如此無常?
陸川一直在想死的人應該是自己,是葛路明替自己擋了一劫。整夜整夜,陸川睡不著覺,想生與死,想通了的時候,陸川忽然就變得淡泊、從容,像一粒堅硬的石頭,足可以抵御一切外來侵略,有著堅硬的外殼,同時也有著一顆柔軟的內心。
關于《可可西里》還有著這樣一個故事:他和美術在選景時車陷在沼澤中,他們步行了十幾個小時來求救,沒想到在戈壁灘上,居然有一個太陽能的IC電話亭。他們一遍一遍地撥著電話,終于在太陽下山之前,他們撥通了電話。
“電影其實就是真實人生的一部分,它就跟你每天說話一樣,是一種真正的表達,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喜歡電影,其實是想利用這種最有力的手段去說自己的話,我是想做一個有自己獨立聲音的電影人,那聲音不是溫柔的,不是偏頗的,而是強有力的。”
如果有一天,《可可西里》就像擊中陸川那樣擊中了你,那么你不妨看看陸川拍攝的過程,因為為了它,他愿意付出他的生命。
(王 暉摘自《大眾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