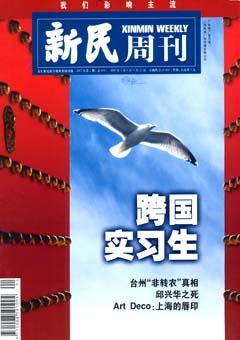滋養大師的土壤
熊丙奇
前不久進行的高等教育座談會上,溫家寶總理向參加座談的幾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說出了他“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大師級杰出人才的培養問題。
溫總理的焦慮,實則是眼下中國大學發展,甚至是整個教育的“焦慮”。想到多年前,高校一窩蜂地響應“號召”,開始“造就”、“培養”創新型人才,并推出“創新人才培養工程”、構建“創新人才培養體系”,設立各類“創新學分”,創新出“創新性一票否決”,筆者意識到,一旦培養大師、造就大師口號深入人心,隨之而來的就可能是各種工程、各種點子、各種名堂。大師級人才,是無法這樣去造就和培養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出大師級人才,靠的是人文滋養。
人文滋養來源于鼓勵個性發展的價值觀念。到今天為止,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教育妨礙著學生的個性發展。某個學生喜歡玩昆蟲,家長會一把將其抓回家,告訴他學習英語、數學和語文才是他的正事;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極力主張抹殺學生的個性。除了少數有自主招生權的高校之外,每年500多萬進入大學校門的學生,至少有99%以上,要求通過統一考試達到一定的分數門檻,無論學體育、學藝術、學文學、學科學,均是如此;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念也影響學生的個性發展。人們習慣于學生苦讀“圣賢書”成才,卻看不慣某個人唱唱歌就走紅、跑跑步就成名,人們習慣于贊揚“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卻視“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而不見,“鄙視”“一夜成名”,人們習慣于把大學當作成才的唯一途徑。筆者對各個學科領域諸如美術、音樂均要培養博士、碩士很是理解,學歷不高,層次就不高。現在,幾乎所有用人單位都把學歷標準作為用人的要求之一,也就成了情理中事。可以想象,在這樣的價值觀之下,個性發展是多么困難的事,個性人才又是多么難以生存。不上大學、沒有學歷,生存都將困難,更何談成為杰出人才。
人文滋養來源于注重啟發引導的培養理念。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以記憶能力代替了學習能力,以學習能力代替了觀察能力、思維能力、想象能力、創意能力。只知記憶、背誦的學生進入高等教育階段,也延續了以前的學習方法,要么以考研為目標,努力攻克幾門考研課程;要么以專升本為學習目的,一進大學校門就準備“第二次”高考,而沒有以上升學目標的學生,則很多時間在茫然中度日。
人文滋養來源于激勵探索精神的考核體系。我國的教育考核與人才評價,都傾向于鼓勵學生“聽話”,鼓勵人才“老實、本分”。聽老師的話、聽家長的話,按老師和家長的話去做的孩子,就是乖孩子,就會受到表揚。學生聽到最多的,是“不準”,“不許”,“不能”,“不要”。
上課不許“亂說話”,大人場合不能“亂插嘴”。久而久之,老師和家長的選擇代替了學生的自主選擇,老師和家長的管理代替了學生的自主管理,老師和家長的意志代替了學生的自我意識,學生們變得沒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己的主張。中國大學課堂上,如果老師在課堂提問,超過半數以上學生低著頭擔心被點名的極其普遍,更不用說學生自主提問了。就是博士生寫論文,也必須“中規中矩”,否則要是有一位“專家”說你格式不規范、觀點太偏頗,就可能被“斃”——這同樣適用于大學教授們進行課題研究,申請課題必須投立項者所好,而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研究本身的規律去進行。我們的人才評價,依舊強調老實、本分,只關注人才對規則(規則的制訂本身也存在問題)的執行,比如全勤、比如工作態度踏實,這導致人們以不出問題為標準,畏懼失敗而不敢去探索、去創新。
在這方面,也許我們可以從國外對人才的評價中找到答案。美國3M公司有一條“15%規則”,允許每個技術人員可用15%的時間去“干私活”,即搞個人感興趣的任何東西,不管它是否與工作有關,是否直接有利于公司。只要你喜歡、感興趣就行,比如,做膠帶研究的可以去做機械研究,這在公司里被認為是非常正常的,沒有人來指責你,你可以天馬行空。一位世界500強老總,在比較美國人才和中國人才差距時說,美國員工會在完成自己的項目時,同時關注其他同事的項目,并對其他同事的項目發生興趣,這樣會讓他們有更全局的視野,發現自己從事項目可能與其他項目的借鑒與合作之處,而更多的中國員工,則只關注自身的項目,而對其他項目沒有多大興趣,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視野的局限、思維的局限也就形成了他們事業的局限。
綜上可知,大師級人才的培養,并非獨立事件,并非高等學校可以通過一些工程、一些活動就可解決的難題。這需要整個社會、整個教育重新全面思考教育,思考人才培養,徹底轉變教育觀、人才觀,中國的大師級人才就會不期而至。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