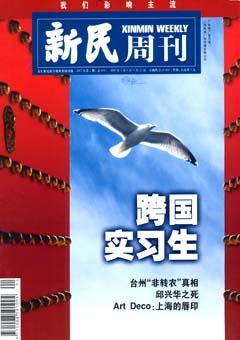Art Deco:上海的唇印
沈嘉祿
不可思議的是,在上海的每個角落,Art Deco的元素與痕跡比比皆是,它早已滲透到上海文化的血液中,奇怪的是我們居然熟視無睹了幾十年。
“如果你打開Google搜索一下ArtDeco,我們可以看到500多萬條相關的信息。”攝影家兼收藏家爾冬強在談起他所關注的藝術現象時,以一貫的激動語調告訴記者:“Art Deco風格從它發軔和誕生的那一刻起,將近百年來,始終有一批狂熱的推廣者和追隨者沉醉在這種風格所營造的優雅、永不落伍的摩登氛圍中。你再跑到街上看看吧,Art Deco無處不在,在歷經多次改天換地的運動之后,它仍然驕傲地挺立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某處建筑或某個家庭之中。”
爾冬強說得沒錯,在美琪大戲院、百樂門舞廳等建筑上,在石庫門房子上,在西洋古典家具和大量的日用器物中,都可以看到Art Deco的鮮明印記。最近幾年,Art Deco的審美價值被重新發現,比如在新天地周邊的新建筑中,這種藝術元素得到了應用并空前強化。
不過,新天地的建筑師們還是比爾冬強慢了好幾拍。早在20多年前,爾冬強在梳理和拍攝上海老建筑時,開始迷戀上Art Deco,并從對建筑的關注逐步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他逐漸發現ArtDeco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藝術風格,更是與上海近代城市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20年來,爾冬強的照相機鏡頭幾乎鎖定了所有上海的Art Deco建筑,還采訪到多位著名建筑師或者他們的后人,并收藏了各種Art Deco風格的器物和家具。這位勤奮的攝影家在游歷世界各地的同時還與世界上Art Deco風格的研究者共同探討并汲取其他城市Art Deco建筑保護的經驗。經過不懈的努力,由他編撰的大型畫冊Shanghai ArtDeco(《上海裝飾藝術派》)面世了,上海的Art Deco遺存也閃亮進入國際視野。
2006年春天,爾冬強收集的藏品作為上海Art Deco的代表參加資生堂在東京舉行的《生存于都市中的裝飾藝術》展覽:2007年1月,他還將攜帶畫冊及此次展覽的照片于美國邁阿密舉辦《上海一邁阿密雙城Art Deco攝影展》:4月在墨爾本舉行的世界Art Deco大會也將出現爾冬強打造的上海Art Deco的魅力形象。
在上海田子坊爾冬強的工作室內,與此同時,一個Art Deco建筑照片展已經拉開了帷幕。爾冬強也許是這個風尚的最后一個深情的回望者,更是敏銳的價值發現者。現在我們可以說,爾冬強通過對ArtDeco的追尋,留住了上海流金歲月的風尚,并且為上海這座城市贏得了應有的榮譽。
記者:Art Deco是如何進入上海并影響這個城市的風尚流變的?
爾冬強:大約是在上世紀30年代,席卷世界的Art Deco風潮登陸上海,上海總是得風氣之先的。這座城市以其飛速發展的自由經濟和永無止境的消費熱情呼應和張揚了Art Deco的精神與個性:摩登、時尚、激進、豐沛、勇往直前……,Art Deco其所蘊含的現代意識和自由精神為上海這座城市投下了巨大的身影和永久的回響,并在上海人的心靈空間里,植入了明代主義自由勃發的激情。
記者:30年代的上海,在今天文化人的演繹下,成了一個流淌著暖意的流金歲月。但歷史又提醒我們,上海的繁榮不能逃避一個大背景:兵荒馬亂、時局動蕩的舊中國。那么Art Deco又怎能在上海奇跡般地繁榮起來?
爾冬強:其實,近代上海的發跡在世界城市史上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喪失部分主權的情況下,由英美合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組成三方共治上海的格局。隨著外國資本的滲透和中國民族資本的壯大,中國各地的移民和外國僑民大量涌入,人口迅速膨脹,上海經濟進入了急速發展的時期,大規模的現代都市營造開始進入高潮,上海迎來了它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記者:如此說來,上海接納Art Deco是有文化基礎的?

爾冬強:是的,上海是近代中國的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翻開《1930年的海關貿易總冊》。我們可以看到上海江海關在“海關稅課”的比例占到全國海關稅收的47.97%。上海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出版中心,報刊密集,在傳媒業、廣告業推波助瀾的作用下,有產階級斗富比闊,中下階層群起而效仿,在時髦消費主義的主導下,上海又迅速成為消費之都、娛樂之都和遠東地元性和藝術和諧感,展示了前衛的審美模式和愜意的現代生活哲學。對于上海大多數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職員階層以及龐大的市民社會來說,Art Deco藝術風格所營造的現代生活方式,一如好萊塢夢工廠制造的夢幻場景。一場現代主義城市生活的戲區最大的不夜城;華洋雜居、五方雜處,東西方文化在沖突交融中,形成一股現代城市文明的潮流。正是在這樣一個當口,以Art Deco為代表的世界風尚裹挾著現代工業文明的轟鳴和美國爵士音樂的鼓點登陸上海,Art Deco以其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多劇在30年代的上海隆重登場了。

記者:Art Deco在上海的亮相通過哪些載體?市民們持何種態度?
爾冬強:主要由美國制造的一系列新鮮玩意,帶著現代城市文明的理念大舉入侵上海城市的公共空間和私人的客廳、臥房(起碼在職員以上的階層),在生活起居和視覺、聽覺上占領了主導地位。ArtDeco風格的設計者們帶著他們對幾何圖形交錯排列的迷戀和對動感、曲折、圓滑、線條和細節的狂熱,將裝飾派藝術極度優雅化和時尚化,這種帶著Art Deco精神符碼的設計思想,猶如一道陽光,照亮了那個時代一切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層面,從飛機、火車、輪船、汽車、建筑的設計,到室內裝潢、家具、家用電器、生活器皿、服裝造型,到音樂、繪畫、戲曲、電影等文化生活。
上海造就了這樣一個市民社會,不管他的出身是資本家、職員還是工人、農民和軍人,他的骨子里對現代文明、時尚生活的認同度都是其他城市市民不一樣的。由此也一度使上海人對擁有上海戶籍身份產生了狂妄的自大,仿佛上海城市以外的人都是“鄉下人”。可以說,Art Deco藝術風格徹頭徹尾地左右著當時上海人的審美情趣和價值觀。
記者:建筑是不是Art Deco風格的最重要體現?
爾冬強:不錯,上海Art Deco建筑的設計主要來自于最著名的設計事務所和洋行的貢獻,匈牙利設計師鄔達克和法國設計師P.費色爾也是這一時期最為活躍的人物。在上海的這一撥Art Deco風格的建筑浪潮中,中國建筑師同樣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為我們城市設計了一大批時尚摩登的建筑,如美琪大戲院、百樂門舞廳、恩派亞大樓、聚興誠銀行、大陸商場、大上海大戲院等等,至今這些房子依然是我們城市各個角落的地標之一。
記者:我們發現,在上海很不起眼的馬路上都可以看到Art Deco的身影,比如正在擴建的河南南路,這一帶過去是貧困人群集中的老城廂,當沿馬路房子拆除后,我看到了后面石庫門山墻上的ArtDeco的裝飾物。你統計過嗎,現在,我們這種風格的遺存在上海還有多少?
爾冬強:很難統計,可以肯定的是上海遺留下了大量珍貴的Art Deco建筑。大多散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大量漂亮的Art Deco公寓和別墅坐落于法租界,而辦公建筑和銀行則位于老的公共租界。它不像美國邁阿密、澳大利亞墨爾本、新西蘭納皮爾、北非阿斯馬拉等城市將Art Deco建筑都集中在一個區域。
記者:今天我們重新梳理并評價ArtDeco與城市的關系,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發展有什么積極意義?
爾冬強:在長達40年的封閉歲月里,上海的這些Art Deco風格的摩登建筑以它現代主義的精神氣質感召和觀照上海人,并逐漸融為上海現代城市精神的一部分。雖然這座城市失去了數十年的發展機會,但是當改革開放的時代來臨時,上海人得天獨厚的現代主義精神和與生俱來的自由創新、文明進步的活力再次得到前所未有的勃發。更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城市建筑的潮流幾度更迭,在發展變遷中許多大都市的Art Deco建筑已經走出人們的視野時,上海的這些Art Deco建筑卻以不變應萬變,得以整體地幸存下來,成為歷史給予我們這座城市的精神遺產之一。
記者:感性地比喻一下,在快餐式消費大行其道、國際風尚各領風騷的今天,Art Deco是風韻猶存的徐娘,還是豐姿綽約的少婦?
爾冬強:我們驚奇地發現在浦東開發的新時期來臨時,上海標志性的建筑金茂大廈和時尚地標的新天地,Art Deco的建筑語言和元素如幽靈一般在一系列新建筑中復活了,這一奇特的建筑現象不能不讓人陷入沉思。
我們還要看到,Art Deco風格在上海已經擁有了眾多“粉絲”,他們熱烈地談論它并躍躍欲試,準備將Art Deco這出傳奇的戲劇重新搬上上海的城市舞臺,看一看上海時尚的地標建筑和那些高檔昂貴的樓盤,你會發現許多新建筑已經貼上了Art Deco的標簽。
我還要說一句,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那一輪大規模的城市營造中,我們收獲了上海Art Deco這個至今仍然可以為之驕傲的藝術風格。今天上海再一次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在城市的大規模改建和營造中,我們能不能給世界再貢獻一個真正的上海風格?我們有理由做出期待。(本文圖片由爾冬強所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