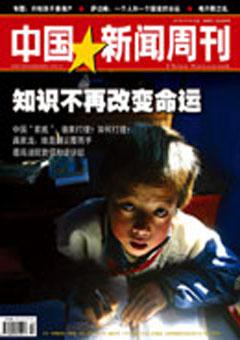科舉式教育之終結
秋 風
上千年來,中國的教育被科舉制度主導,教育成為獲得特權的門檻。今天,隨著市場逐漸發育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科舉化教育傳統終結的跡象終于越來越明顯了,這對于中國社會的結構變遷將有何種影響?
科舉制度乃是君主專制統治的伴生物。科舉的核心是把教育與選官捆綁為一體,接受官方教育、參加官方科舉考試,成為獲得權力最重要的一條途徑。因而,科舉制度開啟了歷史學家所說的中國式平民政治,給了每個人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讓人們在忍受權力的肆無忌憚之時,又時刻幻想著自己通過這場智力游戲進入權力圈子。
如此以來,人們對于教育的關注和投入,必然異乎尋常。人民普遍的信念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教育可以一夜之間改變個人及家族命運的想象,讓整個社會把教育變成了一種拜物教。
這種教育崇拜一直持續到當代。高考制度就是科舉制度的現代翻版。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前,國家控制全部資源,國家雇傭全部大學畢業生,大學成為國家干部預備學校,畢業后即可進入國家機關和國有部門。在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中,這些部門的社會地位和實際收入遠遠高于非現代性部門。如此美好前景激勵著家長、孩子投入激競慘烈的高考競賽中。
中國的教育崇拜傳統與西方的歷史有巨大差異。在西方歷史上,教育由教會控制,經常表示出反對君主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君主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套科層官僚機構進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也就不可能以考試選官。不過,這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多元化格局,從而使近代自由憲政和資本主義有發生、發展的可能。
相反,科舉制度是以權力中心組成一個自上而下的社會,在這里,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僚系統,乃是最優的人生選擇,各種次優選擇,比如經商,與讀書做官的收益極懸殊。而接受過科舉教育的士大夫成為社會的樞紐,但這一集團是純粹消耗性的,需由國家財政供養。因此,科舉式教育具有一種自我毀滅的傾向:受到分享特權之預期的激勵,人們把大量資源投入教育,擠入士紳集團。但一旦該群體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超出國家財政的承受范圍,導致社會危機。
其實,這也正是80年代后期開始政府不得不改革大學生分配制度的根源,因為,政府再也無力為所有大學生提供國有部門的就業崗位和國家福利,只能讓他們進入市場自謀出路。這樣,讀書與做官之間出現斷裂,干部科舉制度即將崩潰。
正是在這個時期,社會開始發生巨大變化,“讀書無用論”幾度浮現。
這種變化在沿海一些私營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最為明顯,在這里,國有部門的收入相對下降,而通過個人創業、出國打工、從事商貿活動所獲得的收入相當高。面對著人生的多元前景,讀書當干部已不再是人生最優選擇,青少年和家庭多了一份選擇的從容,上大學只是出路之一。由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家庭規劃中相對下降了。
娛樂業的快速發展,對人們的教育迷信沖擊也很大。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趕不上三流足球運動員的收入,教授的收入趕不上二流影視明星的收入。丁俊暉、王軍霞更是對書本知識迷信直接發起了挑戰。
另一方面,大學擴招后果的初步顯現,人們逐漸意識到,花了很多錢培養孩子上大學,但國家卻不再提供地位高尚、收入豐厚、分享特權。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尤其是收入較低的農民,不得不開始理性地計算教育的成本—收益,盡管高考-上大學-當干部的想象,仍然驅動很多人不計成本地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資,但種種現象促使人們換一只眼看教育,教育拜物教逐漸褪色。
在干部科舉制度下,人們看到過很多為了供養孩子上大學而砸鍋賣鐵的傳奇故事。這樣的故事固然感人,但終究是教育拜物教下的悲劇。觀念的轉變,或許可以讓很多家庭繞開教育、尤其是高考的致命陷阱,更為理性地安排孩子和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干部科舉制度瓦解,教育拜物教倒塌,開啟了社會健全發育的可能性。
一個健全的社會必然是一種“多中心秩序”。權力、財富、知識、道德等等都是治理所需要的。在這樣的社會,公共治理以民主為基礎,輔之以行政部門的科層制,社會治理以自治為本,經濟、娛樂活動則通過市場機制組織。民主、自治、市場等機制共同治理社會,并各有自己的游戲規則,而不是以知識為惟一標準的。
大體上,民主和自治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選擇機制,自治領袖依靠個人道德聲望脫穎而出,民主代表和行政長官則由民眾通過投票選舉產生:在這兩個選擇過程中,候選人的知識水準并非是那么緊要的問題。
在市場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企業家精神,這種企業家精神不是教育可以傳授的。像蓋茨那樣的輟學生完全可以因其天賦的企業家才能而成為首富。現代發展經濟學宣稱,教育投入積累的人力資本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這當然沒有太大錯誤,但它卻轉移了問題的焦點所在。歸根到底,生產率的提高依賴于競爭,效率來自競爭之下每個人創造性的充分發揮,包括組織創新、工藝創新,它更多地依賴于“竅門”,而不是教育所傳授的書本知識。
因而,在一個健全的社會,教育及由此所獲得的書本知識,與個人的成功之間沒有直通車,對于社會治理來說,知識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中國,人們之所以重視教育,僅僅因為,社會各個領域都由權力組織,權力的命令—服從機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場機制。這樣的社會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種以知識替代民意的戰略,靠一種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來維持其生存,即通過科舉式考試自上而下地選拔官員,通過量化的考核指標——比如GDP指標——自上而下地獎懲官員。這樣,在教育、尤其是科舉考試、在高考,與異常豐厚的收益之間,有了一條直通車,這誘導人們對教育畸形地重視。
今天,人們總算看到一些社會結構良性變化的跡象:市場的發育最為迅速,雖然問題多多,但許多人已經在私人企業中生活;民主在基層發育,自治也在鄉村和城市社區艱難推進。這些領域的分配機制與是否上過大學、考試成績是多少,沒有直接聯系。這些領域的進入不那么看重學歷門檻,是否受過高等教育,對于人們在這些領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確實“無用”了,也即,讀書不再有當官、當國家干部之用,此種讀書無用論,乃是在社會趨向多元化過程中教育回歸常態的撥亂反正之論。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長自愿選擇不上大學,而去經商、從事社會服務、做技工學徒,那時,我們的社會就基本走出科舉時代,像一個正常的社會。隨著教育拜物教褪色,社會趨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歸其正常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