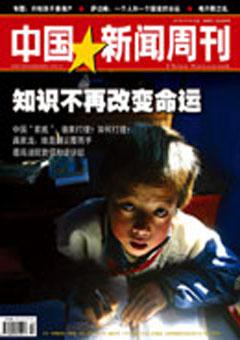“超載”北京須走出歷史生態
薛 涌
北京最大的軟肋,就是政治地理結構所造就的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使首都擴張到不能自我維持的程度,必須依賴其他地區輸血
最近讀到一篇報道,說北京人口嚴重超載,現在已經超載100萬,到2010年將超載300萬。據說解決的方案是雙管齊下:“一是控制人口增長規模,二是大力提升首都環境的人口承載力。”
這種解決方法是治標不治本,沒有觸及北京嚴重超載的深層原因。要了解北京的問題,必須有歷史眼光。首先,要看看中國歷史上的首都生態;其次,要具體看在首都生態框架中的北京問題。
中國古代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傳統,盛世之都也是龐大帝國的權力中心。比如唐代的長安,人口達100多萬,加上周邊地區駐守的大量軍隊,給生態帶來嚴重的壓力。長安的生存,要靠東部(安史之亂后是南部江淮一帶)農業中心的供應。而以當時的技術條件,運輸物資由東向西逆流而上又是談何容易!唐代的皇帝,常常要攜宮廷到洛陽“就食”。682年關中地區饑荒,高宗就讓太子留守長安,自己率宮廷到洛陽“就食”。最為戲劇性的是在786年,關中糧倉空空如也,禁軍領不到糧食,威脅嘩變。在這個節骨眼上有米運到,德宗大喜過望,跑到東宮對太子狂呼:“吾父子得生矣!”
我們現在談起大唐,無不稱那是中國文化的高峰,世界第一帝國;談起長安,也視之為世界第一城。但是,就在這盛世背后,皇帝有時活得像個要飯的,乃至有生命的危險。為什么呢?因為在中央集權的架構中,權力的集中帶來人員和資源的集中,致使首都地區的生態嚴重超載,無法自養。
這一情況,后來也并無根本的緩解。宋以后,中國的政治中心北移,北京成為金元明清四代之都。同時,經濟中心南移,江南成為最為富庶的地區,也是帝國最重要的物資供應地。江南的資源,通過大運河源源不斷地運到北京,維持著北京的生存。這一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脫離的格局,使北京乃至整個帝國變得外強中干。
鴉片戰爭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卻被英國的一支跨越半個地球作戰的艦隊所擊敗。為什么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大運河成了帝國的血脈,即使在和平時期,大運河頻頻淤塞,南糧北運一直充滿了危機。而英國的軍艦一駛入揚子江,兵臨南京城下,切斷了江南漕運的路線,就等于卡住了帝國的喉嚨,清廷除了投降,也沒有什么路可走了。
北京傳統上并非是一個經濟中心,最后成長到中國數一數二的城市,是政治的需要。帝國的防務中心在北方邊境,大部分軍隊都集中在這里,以武力作為統治基礎的皇帝不能離自己的軍隊太遠,所以首都就設在長城腳下的北京。
現代中國和帝國皇權時代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傳統的政治地理,一經形成就有長期、頑固的連續性。定都北京,就必須面對幾百年形成的塑造了北京的政治地理,認識其來源和制約,以尋求解脫之道。說到底,北京最大的軟肋,就是政治地理結構所造就的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使首都擴張到不能自我維持的程度,必須依賴其他地區輸血。而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這個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因為計劃經濟的模式變得更加嚴重了。凡是一些有全國意義的大項目,如亞運會,奧運會等等,必須北京先辦;這樣,萬事都在北京起步,人口當然也就滾滾而至了。
北京的出路,在于打破傳統慣性。改革縮小了政府的職能,也要求中央適當放權,最后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在這樣的發展中,北京就切忌事事出頭。舉個例子,為什么亞運會,奧運會都要在北京舉行?這類傾注全國財力的盛事,難道不能交給別的地方辦嗎?美國辦過幾次奧運會。哪次在華盛頓舉辦呢?在市場經濟中,中央政府的職能更像個裁判,而不是運動員。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也不應該與其他地區爭利。
如今科技發達,像唐代那樣斷糧的事情不可能發生。但是,現代化并沒有改變北京的基本生態結構:北京缺乏水源,缺乏綠化,頂著裹挾著大量黃沙的西北風,處在沙漠化的邊緣。人多喝一口水,樹就少喝一口水;多一畝住房,就少一畝綠地或森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北京還事事盲目領先,那么水源,空氣,交通等硬件就會將這個偉大的城市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