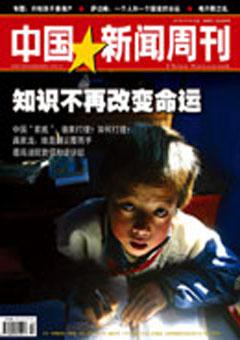他人的生活
王 強
與幾年前風靡世界的另一部德國電影《再見,列寧》不同,《竊聽風暴》并非是對昔日東德的懷舊之作,相反,它揭示了東德政權丑惡的一面
《竊聽風暴》是2006年德國最風光的一部電影,叫好又叫座,獲得了四項巴伐利亞電影節大獎,七項德國電影獎,被認為是爭奪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大熱門。
與幾年前風靡世界的另一部德國電影《再見,列寧》不同,《竊聽風暴》并非對昔日東德的懷舊之作,相反,它揭示了東德政權丑惡的一面:東德秘密警察對其公民實施的全面監控。東德政府當年對其民眾的監控程度之大,令人震驚:在總人口1800萬的東德人中,有600萬人受到秘密警察的監控,相當于每3個東德人中就有一個受到監控。
《竊聽風暴》開始于1984年,是柏林墻被推倒前的5年。東德秘密警察韋斯勒奉命對作家德雷曼及其女友西蘭進行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監聽,希望找到作家反政府的“罪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監聽過程中,韋斯勒的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反而同情其監控對象,于是發生了一系列奇特的事件。
窺探他人的生活,這是電影中經常使用的一種故事模式,希區柯克的《后窗》、科波拉的《對話》和奇耶斯洛夫斯基的《情戒》都是這方面的經典之作。《竊聽風暴》采用了這一模式,有什么創新之處嗎?
希區柯克等人電影中所表現的窺探,更多的是一種個人行為,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關系不大。《竊聽風暴》則不同,它所反映的竊聽具有非常明確的社會歷史背景,是與特定的社會體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影片中的竊聽活動,是由政府組織進行的,是一種體制性的群體行為。作為執行竊聽行為的秘密警察,他們與被監聽對象并沒有個人情感的糾葛,他們只是在執行任務。但是,影片讓我們看到,監聽行為不僅對被監控者形成巨大的傷害,而且也會毒化監聽者的心靈,使他們喪失人性。
表現冷戰結束前東歐社會的電影,為了討好西方,很容易落入一個善惡二元對立的模式,變成抽象的自由觀念的圖解。《竊聽風暴》在這方面處理得比較好,沒有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
《竊聽風暴》在處理作為正面人物的作家德雷曼及其女友西蘭時,沒有把他們塑造成英雄,而是很真實地寫出了他們普通人的一面,他們的無奈和怯懦,他們在片中幾乎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他們真正打動人的,就是對真愛的渴望,對現實的關注。
而有意思的是,韋斯勒這位精明干練的秘密警察,當他通過監聽逐漸了解了德雷曼和西蘭的生活后,對身為女演員的西蘭產生了興趣,正是她的不幸遭遇,使他開始懷疑自己為之服務的政權。
西蘭是東德一位著名女演員,她的美麗引來了東德文化部長的垂涎,這位部長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迫西蘭每周一次與他約會。為了徹底占有這位美麗的女演員,部長才下令監聽西蘭的男朋友,想要借機鏟除他。
韋斯勒在監聽過程中,發現了這一內幕。影片中有一場戲,德雷曼知道女友西蘭與部長的關系后,非常難過,但他沒有責備西蘭,只是請求她不要為了他做出這樣的犧牲。這是全片中最動人的一段對話。韋斯勒也被深深打動,開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說,正是西蘭的美麗與不幸,喚醒了韋斯勒心靈深處的良知。這樣處理比較真實可信。
《竊聽風暴》一片在色彩的運用上頗具匠心。整部片子的色調非常灰暗,尤其是在韋斯勒出場時,都采用的是冷冰冰的灰色,色彩壓抑單調,暗示出這一人物內心的麻木冷酷。與之形成對照的,則是德雷曼和西蘭家中的環境,色彩明亮,暗示出他們兩人的生命力。
英國著名作家奧威爾在其經典小說《1984》中,描繪了一個噩夢般的、公民受到全面監控的社會。進入21世紀,科技的發展似乎印證了奧威爾的擔心,借著反恐之名,西方政府對公民的監控越來越全面。這一現象日益引起人們的警惕,如何防止政府濫用權力,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竊聽風暴》描述的是一個過去的時代,但是,誰能保證類似的現象不會重現呢?這也許是本片更深一層的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