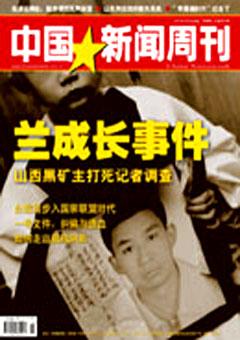傳統文化,喧囂未必是回歸
張 檸
不論文學、藝術,傳統或是大眾文化,如今在市場的消解下統一成了“消費文化”。
娛樂,是公眾視野中眾神追求的代名詞
去年歲末,德國漢學家顧彬語出驚人:激烈批評中國評論家狂捧的《狼圖騰》讓中國丟臉;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中國作家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等等。
當代中國也有好的不錯的作家作品,但在商品市場和大眾閱讀趣味的擠壓下,他們已經非常邊緣,非常低調。
2006年的中國文學以一種極其怪誕的娛樂式狂歡,表達了一個文學繼續淪陷的主題。在其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文學,而是對一種粗制濫造的文學商品的消費,以及對炒作出來的文學事件的消費。人們對文學和意義、審美的關系已經毫無興趣。
文學在淪陷繼續惡搞
“80后”創作現象,依然成為2006年文學爭論的焦點之一。但是,對“80后”的批評一直缺乏有效性,他們或者錯誤地將文學市場當做文學,或者借“80后”來批評當代精神。“80后”代表人物韓寒,毫不猶豫地公開表達自己對老一代占據的文壇的鄙夷,原因是有市場撐腰。從“文壇是個屁”到對當代詩歌說“死了”,韓寒表現了自己作為一個“壞孩子”的破壞能力。
在這種破壞面前,文學又能做什么?3位曾經被歸入“先鋒派”的小說家以自己的作品給出了答案。蘇童一本《碧奴》成為觀念大于文本的典范。《兄弟(下)》在上海書市創下了簽售兩場的紀錄,市場反應與作品評價的反差,使余華看上去更像是陳凱歌那樣的“大片制造者”。洪峰則以乞討的方式,將其與當地文化局的緊張關系公之于世。這是一個令他的晚輩忍不住要嘲笑的舉動。
去年10月,河北女詩人趙麗華的一組口語詩掀起文學娛樂和“惡搞”的高潮。在對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對文學藝術的消費之中,“惡搞”依然是一個關鍵詞。
“搞笑”是第一要義,此類作品中,大都是作者在無聊時制作的“搞笑”產品,并不承載意義,比如《大史記》系列、小胖系列、猥瑣男系列等,它們與精神先輩日本卡通《蠟筆小新》、無厘頭電影《整蠱專家》、相聲《黃鶴樓》等如出一轍。在一個文化權威被遭懷疑的環境里,瓦解權威、嘲弄權威就成了意義?于是,這種搞笑游戲很快與戲仿、拼貼、反諷的修辭方式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批評工具。
不過,“惡搞”并不能涵蓋這一類作品的全部意義。這個名詞首先將自己定義為“惡”,當所有人都假裝擁抱“善”的時候,還有人標榜“惡”,是不是更為真實呢?在一個善惡被真假取代的文化中,“假”就是“惡”的。
“通俗史熱”與教育失落
另一方面,傳統文化通過文化明星的暢銷書,以及歷史題材的電視連續劇,教育消費和民間辦學等各種渠道,進一步切入了公眾的視野。
《百家講壇》的興盛使媒體與學界出現了關于“學術明星”的爭論。加上《大國崛起》《故宮》《大明王朝》熱播,以及《明朝那些事》的網絡閱讀,有媒體稱“通俗歷史熱”已經到來。
可這些爭論并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盡管電視講座容納了文學、歷史、文化甚至社交禮儀等內容,最初引起關注是由于劉心武與紅學會之爭,但真正帶來利潤的卻是易中天、閻崇年等人。而這一熱潮不過是公眾對基礎教育中的歷史教育不滿的結果。他們試圖通過一種新型的大眾傳播節目(通俗演講或電視劇)彌補傳統文史知識的不足。可見,對“五四”以來反傳統思維的反思,已經由學術領域進入了公眾領域,進而來到了文化消費領域。
國學經過兩年的預熱和炒作之后,在2006年終于找到了最輕便有效的贏利模式。鄭州、武漢、深圳相繼出現“童學館”,將國學教育變成狹義的傳統蒙學教育。
電視談話節目里關于“孟母堂”的討論,打破了國學家教課程的安詳面孔。包括薛涌在內的支持者引用美國“家庭教育”的模式指出,家長擁有選擇孩子教育方式的權利。這一辯護漏洞在于,他們沒有發現那些“蒙學迷”式的家長所求的,并非兒童教育中的自由理念,而是在追求更高層次的、不那么容易被察覺的約束。
家長的這種需求,并不是一種更為先進的教育思維,而僅僅是對基礎教育的不滿,又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他們將問題交給古人,交給別人,成了他們置身事外的惟一選擇。這樣做的結果是,國學被等同于蒙學或古漢語修辭技巧,而喪失了原有的經世濟民的宏大意義與獨特的知識趣味。最終,傳統文化教育也只能變成一種新型文化經濟,乃至一種標識兒童家庭身份的消費方式而已。
那些主張“孟母堂”是古典教育模式的人,大多屬于富裕家庭,教育對象是兒童。而普通家庭的學生最關注的問題,依然是現實利益。多數入學和就業者,并不考慮教育與傳統的關系,他們幾乎清一色選擇香港大學和出國留學作為出路。
“如果同時被香港知名大學和內地一流高校錄取,你愿意選擇到哪里上學?”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和新浪網站考試頻道在2006年高招期間的聯合調查顯示,選擇香港高校的學生和家長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71.2%。中國教育界第一次遭遇真正的競爭,人們產生了清華、北大是否淪為中國二流大學的疑問。
選擇中國傳統教育方式還是現代西方教育方式更有利于青年一代成長和國家的前途,這個問題太抽象。在普通教育問題上,入學和就業是一個基本的試金石。教育投資是否能夠獲得相應的回報,將那些烏托邦式的教育理念打得粉碎。
盲目的娛樂狂歡
教育領域的激烈爭論中包含了諸多憂慮。娛樂領域則是一派盲目樂觀。在這里,娛樂成了公眾藝術追求的代名詞。
電視“選秀”成為地方電視臺繼“豐胸廣告”之后又一件贏利法寶。除“超級女聲”“我型我秀”等傳統選秀節目之外,國內至少8家省級衛視新推超過10種全國性電視選秀節目。盡管后來者甚多,但“超級女聲”臨近尾聲時鬧出的運營商之爭,顯示出這一品牌在未來若干年內的營利潛力。與之南北并稱的“加油!好男兒”在商業開發上更為赤裸。這一活動將女性需求塑造為篩選模型,并在活動過程背后,拼湊出一個“女強人”的幻影。它最初被貼上了“男色消費”的標簽,并因此受到女性主義者的贊譽。但比賽結束以后,主辦方卻以慈善為名,在某在線交易網站公開叫賣優勝選手的約會。若即若離的男色想象,由此變成了一次試探性的交易活動。為了最大可能地獲得利潤,制作單位異常謹慎地向選美挪了一步。
2005年,“超級女聲”在公眾與學者中得到令人詫異的好評,認為是一次“海選”的預演,但直接的收益主要體現在市場領域。2006年,“超女”粉絲們又一次早早地用手機淘汰了那些“最優選項”。許多優秀的歌唱者即使有評委的保護也無法進入最終階段。這種“娛樂民主”的結果,是一代或幾代中國青年音樂審美能力的體現。短信票數不過是一面“風月寶鑒”,照見了一代人基礎教育的漏洞和精神背后的骷髏相——獨立判斷和自我意識的缺失、審美能力的下滑。
娛樂狂歡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盲從取代了另一種盲從,一種控制取代了另一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