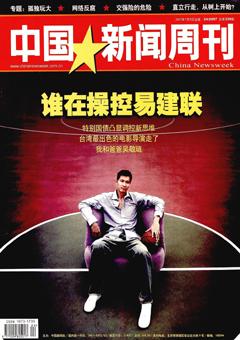孤獨玩大
羅雪揮

那些“抖空竹”、跳皮筋、丟手絹的簡樸“老兒戲”,變成了物質匱乏年代的象征,只有在老胡同和遠離城市浮華的偏遠地區,還保持著生機。而伴著豪華玩具和虛擬游戲形單影只長大的一代,又失去了什么?
“讓我們借助一句歌詞來開始吧!想起來是那么遙遠。或者讓我們以講故事的方式來開頭好嗎?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時候還是上個世紀呢……”這是今年6月舉辦的北京潘家園懷舊玩具展上的廣告語。
在這里,各種老玩具雜陳:空竹、九連環、木頭彈弓叉、毽子、沙包、拐,甚至有標價為一角六分的兒童棋……參觀者,常常是帶著孩子來的家長。這些家長們,通常是急匆匆走進展室,而后腳步又突然慢下來,會心地露出一笑;而他們的孩子們,則像是有組織似的,轉了一圈,就齊刷刷地坐在了展廳的電視機前,目不轉睛地盯著屏幕上正在播放的動畫片。
當成人們站在兒時的玩具前情緒激動甚至傷感時,孩子們坐在那里彼此間并不交流,只是隨著劇情偶爾發出笑聲。
在他們的身后,蒙著歲月塵埃的老玩具,真正地成為了陳列品。
誰還在玩“老兒戲”?
當今的城市兒童,玩的是芭比娃娃、樂高玩具、電子游戲。那些依然在“老兒戲”中流連的,只是處在物質相對匱乏中的孩子們。從事青少年素質教育工作的任偉告訴記者,他不久前去四川松潘時,看到一個村子里的小學,孩子們還在玩像“摔紙包”這樣的簡樸的游戲。“孩子們玩得很自然,因為他們沒錢買玩具,那里也沒有商店。”
在新疆一所農場小學任教的張葉介紹,那里的女孩們還在跳皮筋,男孩們還在玩玻璃彈球。只是這樣的游戲也隨著時代的發展有所“分化”:以前的皮筋,都是用老輪胎剪成的,現在有彩色皮筋賣,一塊五一根。
家庭條件稍好些的孩子,比如那些住在場部的孩子,買得起皮筋,但往往跳得不好,只能夠當“柱子”,負責帶皮筋和撐皮筋,而條件差一些的孩子,要想玩皮筋,就得靠自己的實力,一關一關地跳下去。所以,真正跳得好的是這些“窮孩子”。
在北京,“抖空竹”這種“老兒戲”也還有人在玩。出身北京空竹世家的李連元,就在北京宣武區新橋胡同里的老墻根小學收了16個徒弟。當記者來到這所小學時,看見了幾十個孩子正在一起抖空竹。他們花樣迭出,空竹“嗡嗡”的聲音交織在一起,猶如音樂合奏。師父李連元夸道:“我父親比我爺爺玩得好,我比我父親玩得好,現在我的徒弟比我玩得好。盡是新花樣。”
宣武區新橋胡同,曾經是當年老北京空竹的發源地。現在站在胡同里放眼望去,不時能夠看到大大的“拆”字,頹敗的老房子與首都的繁華咫尺相對。然而,這些抖空竹的孩子們卻不再是純粹的“老北京”。
老墻根小學的校長呂仕珍介紹,老墻根小學有190多名學生,將近70%都是外來人口子弟,北京籍的學生則源自周邊老城區,家庭經濟條件相對都不是很好,家長一般不會給孩子們買高檔玩具。
據呂仕珍觀察,孩子們平時的游戲,一如數十年前的情形,也就是在胡同里跑跑跳跳,男孩子玩沙土,女孩子頂多跳跳皮筋。老墻根小學三年級女生曹元告訴記者,她常玩的游戲除了抽漢奸(陀螺),還有跳繩,做仰臥起坐。而如今,老墻根小學的孩子們人手一個空竹,“空竹便宜,簡單易學,孩子們也覺得很有樂趣。”呂仕珍介紹。
“抖空竹”已經申請加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孩子們為此勤學苦練,師傅李連元甚至希望將來這些抖空竹的孩子能夠走出國門。而這些擔負“老北京”文化形象的孩子們,甚至很多還不是戶籍意義上的“北京人”。
富裕的孩子一個人玩?
“馬蘭開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建國后,從南到北,從教授家庭到工人家庭,中國兒童都是齊刷刷地哼著童謠,一窮二白地長大。
北京城管隊監察員,生于1973年的著名“玩家”唐惠民表示,他如今收藏變形金剛,“有報仇的心理”,“當年買不起的,如今都收藏起來。”
唐惠民們將補償的心思更多地放在了孩子身上。他們為孩子購買包括鋼琴在內的各式高檔樂器,各種昂貴的電動玩具和百科全書,中國城市新銳階層的下一代,與父母的童年相比,幾乎是有求必應,但大多都是玩具成群,形單影只。
出生于上個世紀70年代,現任北京一家廣告公司負責人的林慧還記得自己和小伙伴把廢報紙團成團當排球,在兩棵樹上蕩秋千可以蕩一上午的快樂時光。可是當生活進入房車俱備時代,四歲的女兒也進了價格昂貴的雙語幼兒園時,她頭疼的是女兒的玩具太多,卻好像沒有什么特別喜歡的。
她總是安靜地一個人玩,這些游戲固然好,林慧表示,但是玩具都是獨自玩的,到底有問題。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人將來就是天大的本領,沒有人合作也無濟于事。
家長們對于孩子安全的極度擔憂,也是孩子們獨自玩游戲的重要原因。上瀕翅膀科技(北京)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家從事兒童素質教育的公司,其董事長蘭海回憶,以前放學大家都和小朋友結伴回家,一路走一路玩,如今都是家長去接孩子,放學立即就要和小朋友說拜拜。
59歲的四川退休教師馮高瓊對此很擔憂。她幫著女兒在美國帶孩子時,孩子每日有半天的時間都是和小區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而如今回到北京,關于孩子被拐騙的消息層出不窮,膽顫心驚的家長寧肯將孩子圈養在家里。馮高瓊很擔心這種狀況持續太長,“孩子成天關在家里,不跟小朋友玩,將來就不懂得什么叫謙讓和互相幫助。”
而沒有伙伴的中國城市孩子事實上也沒有時間玩。北京一所大學附屬幼兒園的大班孩子,在走廊上貼出了“我的晚間小計劃”,大部分孩子晚上都要練習至少半個小時的鋼琴,計劃中還有學英語,還有讀書,再加上看電視,余下的只剩下洗漱睡覺了。
“我覺得還是自己玩比較有意思。”10歲的北京小學生鄭西宣布。如今,鄭西的最愛是MP3和“拓麻歌子”。后者簡稱“拓麻”,是源于日本的電子寵物,它可以虛擬人的一生,從嬰兒到成人,甚至還可以結婚生寶寶。和其他流行的游戲一樣,“拓麻”當然是一個人的游戲。而正版的“拓麻”需要一百元以上,無論是在中國的特大城市還是二線城市,甚至遠到徐州和蘭州,擁有一個正版“拓麻”都是時尚小學生的象征。
孩子們早已經適應了沒有“伴”的游戲生活。在中國的大、中城市里,小學里早已經沒有了“丟手絹”的歌聲,只有一種叫“手絹花”的游戲,就是一塊六角形的可以頂在頭上轉的布,“最適合一個人玩。”曾經讓小伙伴們一比高低的陀螺則發展成為電動的玩具,孩子們各自玩各自的,默默地“劃地為限”。北京中關村一家玩具店的老板告訴記者,新玩具都是一陣陣的,流行的時候小朋友都來買,人手一個,比如“拓麻”,且互相攀比,可是這些玩具頂多“熱賣”幾個月,很快也就過去了。
即使仍然在玩“老兒戲”的孩子,也向往著代表新物質的虛擬游戲。遠在新疆,13歲的劉靜剛剛告別小學時代,并且獲準可以偶爾去打電腦游戲,她表示,如果要論喜愛程度,電腦游戲還是首當其沖,因為“不需要大家一起玩,能夠找到現實世界無法滿足的充實感”。
“老兒戲”漸漸被城市的浮華淹沒,或者干脆被新時代收編。《老兒戲》的作者何誠斌曾試圖用文字記錄下過去年代一個個快樂的游戲,包括跳繩,但當他告訴女兒“我們班的女生,沒有哪個不會跳繩子”時,女兒的回答讓他瞠目結舌:“你們班上的女生,會上網玩游戲嗎?現在網上就有一種跳繩子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