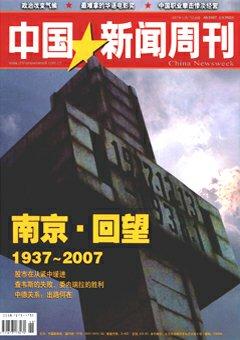老蔡是誰?
邱志杰
陳宗光筆下的老蔡,是人到中年的中產小人物,他有可能但不一定會因工作透支而過勞死,但一定會因為生活過度而死

陳宗光畫一個叫做“老蔡”的中年男人的困境和焦慮:他總是失重,心事重重;他百般努力卻難于保持平衡;他從一個封閉空間飄蕩進另一個封閉空間,空間總是太小,光線總不夠亮麗;他被周遭的物品包圍著,他依賴它們卻又被它們糾纏,無力控制;老蔡忙碌,可這不過是優(yōu)柔寡斷的結果;老蔡很低調,但心中常有狂野的沖動;大家都覺得老蔡很理智,但老蔡有點害怕自己;老蔡顯得很健康,但老蔡自己對此疑神疑鬼。總之,“老蔡”是一個小人物,一個平庸的人,一個焦慮的人。一個正常的人,一個太正常的人。
我們都曾經(jīng)學習如何畫英雄人物,畫那種典型環(huán)境下的典型人物,那時候我們其實是想畫一個人物的理想。因為有這理想撐腰,畫中人其實總是一個大人物。
工農兵雖小,但他們的理想和事業(yè)遠大,所以他們大。后來,我們學著畫老人、窮人、遠人,畫少數(shù)民族,畫皸裂的皮膚和土地,畫污濁的房屋和布料,畫普通人,那時我們其實是想畫一個人物所擁有的文化。因為有文化撐腰,那樣的畫中人其實依然是一個大人物。
小人物在中國繪畫里面遲遲不能登場,是因為理想和文化在90年代中期以前依然盤踞在人們的心中。當電視里的汽車廣告開始炫耀什么是成功人生,房地產廣告開始把房子叫做豪宅的時候,我們知道,小人物在中國文化里重新登場了,甚至成了中國文化的統(tǒng)治者。
于是,中國繪畫里出現(xiàn)了小人物。不過,有的畫家通過畫小人物把自己變成成功人士,而陳宗光通過畫小人物,來理解小人物,理解成功人士的血腥代價。
小人物的話語來自流行文化,他們表達夸張,他們從平庸的生活里很早就知道世態(tài)炎涼,就建立自己的保衛(wèi)機制。他們也在自己的人生中弄出很多情緒來,也愛恨離合。他們只不過焦慮,因為缺少真正的大眾文化。我們的大眾文化只是向大眾炫耀小眾的生活,我們的傳統(tǒng)價值觀破碎了,我們的小人物怎么能不破碎?
對于老蔡這樣人生已進入午后的平庸的中年男人來說,他既不夠有悟性在平庸中看到解脫的道路,也不夠有勇氣對著這場過了幾十年的生涯發(fā)動一場顛覆運動。但他還有足夠的精力來悔恨、憧憬、反省;他也還有足夠的閑情來進行攀比,通過攀比自我折磨。有精力有本錢有閑情這么做,說明老蔡已經(jīng)是一個中產。
中產據(jù)說是我們的社會的主流,是社會橄欖球的肥腰;據(jù)說中產的情緒就是整個社會的情緒,中產的焦慮就是整個社會的焦慮。但是我們的社會顯然還沒有找到好的辦法來阻止中產向上看齊,只要攀比,中產如何可能不焦慮?
他們的中年,不得不變成一種后青春期和前更年期。這就是老蔡,一個焦慮的中年的中產,他不但是一個工作狂,更是一個生活狂。老蔡有可能但不一定會因工作透支而過勞死,但一定會因為生活過度而死,對此他非常清醒,他對自己說:對此,我必須要平靜而幽默地忍受下去。
作為一個小人物,“老蔡”先生可以因為壓力放棄尊嚴。而創(chuàng)造了“老蔡”的陳宗光,卻通過構造老蔡的生涯建立了自己的尊嚴。陳宗光一直在進行有意義的繪畫。“有意義”的意思是:不為了掙錢,不為了評職稱,不出于習慣和教條,不是不得不畫,而是可以不畫卻不妨畫著。畫家通過繪畫這樣的行為,來尋找繪畫本身的意義。這樣的繪畫具有了一種日記體的色彩,既自我催眠,又自我拯救。
不管是在二十年前還是今天,一種循規(guī)蹈矩的、人云亦云的、趨同的生活方式,始終是社會的主流,中外皆然。這才是實驗藝術真正的假想敵。它在二十年前表現(xiàn)為對官方話語的不反思。在今天,表現(xiàn)為對中產階級理想的不反思。
藝術家可以做的就是再次用自己的荒誕,去提醒未來的不確定性。陳宗光對“老蔡”的批判性構造,正是劍指這樣的生活方式。在他的畫面中,中產階級生活,再次被表達為一種理性的牢獄。為此,他煽動了變性的力量,色彩的力量,筆觸的力量,他捍衛(wèi)了繪畫作為思考工具的尊嚴,從而加入了頗具歷史意義的實驗。
(作者為中國美術學院教授、當代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