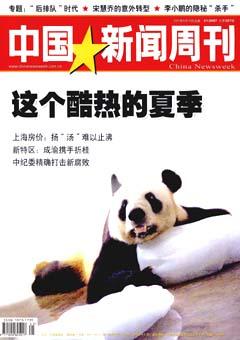高溫的烙印
陳 曉
對于重慶來說,2006年的高溫和干旱并沒有結束———它的“余威”讓這個城市的土地、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迄今無法緩過勁來
自2007年春天以來,重慶市所轄的榮昌縣雙河鎮村民溫云宏每天用電泵從一口深20多米的井里抽水。每次斷斷續續抽半個小時,可以灌滿家中的大水缸。每天抽兩次,夠家里幾口人煮飯、洗衣服等等。
這是榮昌縣政府“紅層取水”工程的一部分。去年炎旱后,榮昌縣政府在農村住戶的屋旁打了3萬口深井。高溫導致土壤失墑,棍子插進土里50厘米,不見一點水汽,原先6~7米深的水井只能留一灘水漬。2007年,重慶市計劃再打井1萬口,要以此解決10萬人的飲水困難。

為了防止水分蒸發,溫云宏用幾層塑料布把井口包得嚴嚴實實,上面還壓上了一塊石頭。但是這點井水救不了屋側的幾畝水稻。因為開春以來一直沒有雨水,水田里沒有一絲積水,秧苗只移栽了3/4。溫云宏的老母親拔下一棵秧苗,在田邊奔走著向人展示它們夭折的命運“根部已經長到半指高,早就過了移栽的節氣,現在只能等它們干死。”
從炎旱到春旱
榮昌縣是重慶地區2006年高溫干旱的重災區,重慶市水利局規劃計劃處處長王振智告訴記者,如果去年9月那場救命雨還下不來,就要動用火車往這個縣城送水了。高溫給這個地區的影響并沒有隨著那場秋雨而結束,它消耗掉了榮昌縣蓄水庫80%的水量。而自此之后直到現在,榮昌縣的降水量僅為100毫米。這么點兒雨水,早就被開春之后異常的30℃以上高溫給消耗掉了。
離開重慶主城區,沿高速路往西,觸目之處,都是西南地區平常的初夏景象。路邊不時閃出一小片枯死的竹子,幾樹一半綠葉、一半焦黃的芭蕉,水田里的蓄水流盡,一些荒地還張著干裂的口子……
這些經歷了去年的炎旱、并經歷著今年春旱的田野里,正在書寫著物種進化論。曾經在這個區域的氣候變化中適應并生存下來的重要作物,在經歷兩季的異常升溫和干旱后,開始不適應這片土地了。榮昌縣救災辦主任秦景英告訴記者,本來被歸為耐旱作物的竹筍,今年減少了70%。桑樹大面積干死,這一季蠶農本該有2700多張蠶種,今年登記的只有20多張。開春的水量只夠50%的水田插秧,種下的水稻又干死了39%。有11萬畝大蔥田改種了更耐旱的玉米。
榮昌縣內最大的一條河——瀨溪河,水面急劇下降,岸邊裸露出一大攤枯黃的水草。由于上游的大足縣也是干旱重災區,瀨溪河已經部分斷流,成為幾段內河,死水上布滿了浮萍。
記者了解到,由2006年的炎旱遞延下來的春旱,影響了重慶30個區縣。其中111個鎮鄉、638個村、117.57萬人、85.83萬頭大牲畜仍存在臨時飲水困難。榮昌、永川、大足這些地處渝西的縣城,居民用水依然靠送水解決。
特殊的“水利設施”
一些延續著古老的氣候規律運行的水利設施,都在遭受著氣候變化的嘲弄。重慶的傳統雨季是5月和6月,開春因為怕4~5月的汛期,重慶市水利局讓農民們不要蓄水太充足,以防洪水。結果這個季節,雨水并沒有到來,“雙河鎮從去年9月到現在的降雨量,總共只有45毫米。”劉定朝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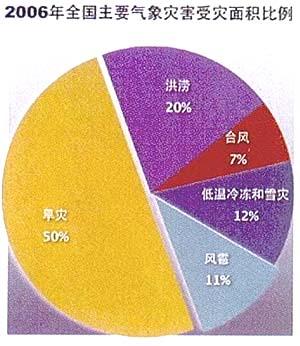
王振智去年一年都在忙著新水利設施的修建。2006年的高溫大旱之后,重慶市投入了70億元人民幣用于水利修建。其中包括各種等級的水庫、修塘壩、打井、截潛流。
但重慶周邊大部分區縣還屬于“吃飯財政”,水利的修建還遵循著“經濟有利”的導向。政府投資的水利修建種類還局限在中小型水庫,以及給農田集中供水的干渠;而散布于城市輻射末端的山區農戶,他們的飲水和農耕用水,還沒有—個萬全之策。
春雨的時節已過,夏日的高溫將至。劉定朝和村民們也修建了一些小水利進行自救。大石堡村每棟房子外都砌了一個水泥大缸,作為儲備生活用水。由于露天放置,水池里已經長出了一坨坨綠幽幽的水苔,粘稠的水面上不停有小昆蟲起降。
雙河鎮政府還投資了十幾萬人民幣,整修了山腰的—個堰塘。這是全村人的水源,但從2006年夏季以來,它就成為了一口大土坑,塘底的裂縫清晰可見。而在雙河村,臨近的一家兵工廠的生活廢水也被用石頭砌成的堤壩攔成—個水塘,以供村民用。
雙河鎮的高處還有一個提供全鎮生活用水的水庫,記者到這邊采訪時,其存量只夠維持全鎮半個月的用水。“我現在最擔心的是生活用水的水庫斷水。”劉定朝說。“氣象預報說過幾天有雨,我們已經做好一切準備了。要是雨下不來,那就沒辦法啦。”劉定朝擼起袖子,露出黝黑的手臂——這是去年在高溫天氣下撲滅山火、在60度的工作環境里騎摩托車送水時留下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