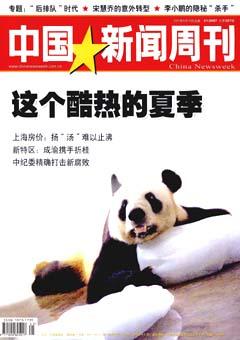減排目標如何實現
李 楊
6月2日,德新社報出消息:美國總統布什暗示,美國可能會同意為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確立一個廣泛的國際目標,條件是中國、印度等能源大國也加入到這一努力之中。
這是多年來美國政府第一次對《京都議定書》做出“積極”回應。報道的副標題把布什的這一計劃表達得更加直白——“核心是把中印等發展中國家拖入談判”。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國際能源組織最近發布的報告稱,預計到2008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因此,一段時間以來,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減排的呼聲很高。布什計劃可以被看作中國在節能減排問題上受到國際壓力的一個最新注解。
參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談判的中國科技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呂學都向媒體坦承:“中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但呂學都認為,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壓力并不單單來自國際社會,國內的能源安全問題壓力更大。過去20多年,中國的能源彈性系數(能源消耗速度和GDP增長速度之比)一直保持在1以下,而2002年到2005年之間,能源消費的總量和強度都在上升,能源彈性系數一度達到了1.5到1.6之間,也就是說,中國GDP保持每年10%的增長速度,能源消耗增長速度則達到每年15%。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十一五”規劃提出,“十一五”期間中國要實現單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目標,其中,2006年的目標是下降4%左右。然而,作為“十一五”開局年的2006年情況并不樂觀,單位GDP能耗僅下降了1.23%,和年初預定4%的節能目標相去甚遠。
“雖然‘十一五規劃中的這個減排降耗目標是我們的國內政策,但它也是中國傳遞給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信號。”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迎對本刊說。
5年降耗20%:一個可行的目標
就在《參考消息》刊登德新社消息的第二天,6月3日,國務院印發了國家發改委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英國《金融時報》對此評論:中國在八國集團(G8)德國峰會召開之前,公布一項期待已久的氣候變化“行動計劃”,是為其環境政策進行更為積極的國際辯護。
在《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中,中國承認,去年全國沒有實現年初確定的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的目標,加大了“十一五”后四年節能減排工作的難度。此外,報告披露了目前面臨的嚴峻形勢:今年一季度,工業特別是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增長過快,占全國工業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電力、鋼鐵、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業增長20.6%,同比加快6.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報告進一步指出,這種狀況如不及時扭轉,不僅今年節能減排工作難以取得明顯進展,“十一五”節能減排的總體目標也將難以實現。
形勢的確不容樂觀。但本來,在相當—部分專家眼中,5年降耗20%的目標并非高不可攀。國家發改委有關專家算了這樣一筆賬: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用能源翻一番支持了GDP翻兩番,平均每年單位GDP能耗降低4%以上。2004年與1990年相比,全國單位GDP能耗下降了45%;火力發電煤耗、生產每噸鋼可比能耗和生產單位水泥綜合能耗分別降低了11%、29%和21.9%。
盡管如此,目前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依然僅僅只有33%。根據官方公布的資料,中國的單位GDP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個行業主要產品的單位能耗平均比國際先進水平高40%;鋼、水泥、紙板的單位產品綜合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分別高21%、45%和12%。
因此,無論是橫向與國外先進水平比,還是從自身縱向發展看,中國節能的空間和潛力都很大。
降耗目標沒完成:誰之過
對于2006年降耗目標未能如期實現的原因,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理事長、中國首任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在此前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直言,主要責任在地方決策者身上。這位知名環保專家說,一些地方部門嘴上說環保重要,但一碰到具體問題就變樣了,仍然是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
山西省環保局公布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93.31%的群眾認為,環境保護應該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然而91.95%的市長(廳局長)認為加大環保力度會影響經濟發展。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的一項調查為曲格平的觀點提供了事實支撐。能源所研究員周大地和他的兩位同事郁聰、白泉對山東、江蘇、山西三個能源消費大省調查后發現,地方追求更高GDP的壓力巨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難以實現。
他們在2006年11月的《中國能源》雜志上撰文指出,“十一五”規劃提出“十一五”期間GDP年均增長7.5%的目標,但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規劃中,GDP的增長速度都高于全國規劃目標,平均GDP的增速在9.9%。不僅如此,地方還層層放大GDP的增速,相互攀比現象嚴重,一方面和相似的省市比,另一方面和以前達到過的速度比。不少市縣提出GDP增長率要達到14%~16%,甚至更高。在這種狀態下,什么項目能快速拉動GDP的增長,就上什么項目,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產業成為口號。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不順利是沒有實現年度節能目標最重要的原因。”周大地說,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工業拉動,服務業比重偏低,而在工業中,高耗能的重化工業比重偏大,這樣,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消耗能源和資源。
周大地在報告中分析,造成地方一味追求GDP的原因,與1994年后實行的中央和地方分稅制有關。分稅制實施后,稅源穩定、稅基廣、易征收的稅種大部分劃歸了中央。實施分稅制后的當年,中央的財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國財政總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總收入比重不斷減少的同時,支出比例卻不斷加大。地方由于需要更多的財政收入支付教育、社會保障等費用,不得不拼命上項目,以增大地方GDP。
需要科學的政策設計
陳迎指出,中國減排指標是一個自上而下提出的目標,在缺少科學評估和具體行動方案的情況下被分解到各個省,然后推動整個社會去完成。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科學決策還不夠。
一位研究氣候變化的專家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了解到的一些情況佐證了陳迎的說法。寧夏的代表抱怨中國東西部省份減排指標分配不合理,稱東部沿海省份把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移到西部,是西部省份完不成降耗指標的原因之一。這位專家還向本刊透露,去年承諾減排指標最高的吉林省,是在沒有事先做好評估的前提下,盲目認領指標的。吉林相關領導曾向國家發改委的專家請教,
吉林能否完成地方GDP能耗下降3(W0的指標,發改委專家說沒經過調研無法評估。盡管吉林對于減排指標心里沒底,但還是倉促認領了指標。
陳迎說,英國有一套促進企業減排的政策,對中國很有啟發。英國政府首先聘請咨詢公司,對主要部門的能源使用狀況及節能潛力等進行詳細評估和定量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制定節能降耗目標,然后將這一目標分解到各個工業部門。
對于企業,英國從2001年起開始征收氣候變化稅。氣候變化稅使企業的燃料費用普遍增加10%到15%。同時,為了鼓勵減排,政府又規定了一些稅收減免措施,比如,與政府簽訂氣候變化協議的企業,若完成規定的減排目標,可以減免80%的氣候變化稅。另外,政府根據《京都議定書》排放貿易機制,在英國國內設立減排交易平臺,讓企業之間進行排放指標的交易。再有,政府利用征收來的氣候變化稅的部分收入創立碳基金,為企業提供貸款、審計、培訓等服務。
英國的各種政策工具給企業一個強烈的信號:氣候變化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主權國家面臨的環境問題、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也是企業面臨的—個經營戰略問題,必須把氣候變化作為生意的一部分來做。
轉變個人消費方式
陳迎提醒,一個節能降耗的方面目前被極大地忽視了,那就是轉變個人的消費方式。“能耗不僅僅是用電、開車這樣的直接能源消耗,”她說,“還包括居民整個消費方式所影響到的間接能源消耗。”
丹麥技術大學的喬根(Jorgen Stig Norgard)教授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直接能源消耗”和“間接能源消耗”的概念。他在《從我做起——走向低能耗社會》一書中寫道,家庭的直接能源消耗主要包括照明和家用電器使用的電、取暖和生活熱水所用的熱量以及汽車和摩托車所用的燃料,但家庭同時還有一種間接的能源消耗,比如購買一塊地毯、一份保險、一捆白菜或一幢房屋,都將導致能源消耗的增加,因為制造、運輸以及銷售以上各種東西都要消耗能源,購買得越多所消耗的能源也越多。
據陳迎研究,在中國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中,工業占70%,居民占10%,剩余部分被交通、農業等消耗掉了。但工業產品最終還是被人購買并消費。從最終結果看,居民能源消費能占到50%到60%。
“我們現在只想到隨手關燈,把空調溫度調高幾度,少開一天車,這只是減少了直接能源消耗。而我們使用—個杯子,這個杯子的生產過程和垃圾處理過程都將消耗能源,這是間接能源消耗。”
陳迎給記者出示了國外的一張能量消耗分析樣本,舉的是一臺電冰箱的例子。一臺電冰箱每年的直接能源消耗為1854兆焦耳,而它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的間接能源消耗(包括生產、貿易、運輸、垃圾處理等)是3484兆焦耳。總體計算,如果正常使用15年,這臺電冰箱平均每年消耗能源2086兆焦耳而如果這臺冰箱只使用5年的話,它平均每年消耗的能源就達到2551兆焦耳,每年高出465兆焦耳。
“眼下青年人的消費習慣、消費觀念處在急劇變化的過程中,需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健康消費觀念,特別需要看到的是,中國資源、環境的壓力,不允許我們追求過度消費。”陳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