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碼頭:在集體記憶的名義下
王 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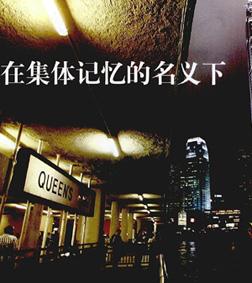
“現(xiàn)代人的感動(dòng),與其說在于一見鐘情,不如說在于最后鐘情?”
——本?雅明
去年11月11日,香港的天星碼頭停航,當(dāng)天有15萬港人乘坐小輪以示緬懷。午夜時(shí)分,數(shù)千人聚集一起,手持蠟燭向碼頭道別。
5個(gè)月后,皇后碼頭也走到了最后一夜。沒有倒計(jì)時(shí),沒有歡送,只有300人拍照留影,規(guī)模小了許多。不過,這淡淡的離愁別緒里卻添加了火藥味。十多個(gè)文物保護(hù)組織成員,將“不告別”的橫幅掛在皇后碼頭的牌匾下,反對政府拆除碼頭。
其實(shí),皇后碼頭的命運(yùn)早已定下。2000年,特區(qū)政府提出發(fā)展中環(huán)的第三期填海工程,為拆遷碼頭咨詢民意,當(dāng)時(shí)沒有多少人反對,如今規(guī)劃定了卻又生出變故。
簡陋的建筑,稀薄的歷史
為什么是“皇后碼頭”而不是“女王碼頭”?香港之外的人多半會(huì)有此一問。意料之外的是,幾位香港友人都無法解答。幾番考證只得到一個(gè)模糊的答案:皇后碼頭可能是為紀(jì)念維多利亞女王而建,只是早年香港一律將女王誤譯為是皇后;也有可能是為喬治五世的瑪麗皇后而建。
既以皇后為名,這個(gè)長方形的碼頭卻實(shí)在有些簡陋得過分。一些柱子撐起水泥頂棚,三個(gè)小型船只泊位。碼頭有一家小吃部,售賣零食和飲品,岸邊有三個(gè)長方形白色的“皇后碼頭”和“QUEEN'S PIER”的牌子。
坊間有個(gè)說法,皇后碼頭與咫尺之遙的愛丁堡廣場、香港大會(huì)堂,都是以一個(gè)英國小鎮(zhèn)的建筑為范本。在上世紀(jì)50年代初籌劃中環(huán)海濱這個(gè)建筑群時(shí),主事者可能做夢也想不到香港會(huì)有今日這般風(fēng)光。
準(zhǔn)確地講,現(xiàn)存的皇后碼頭已經(jīng)是第二代了。首座皇后碼頭建于1925年,1954年就埋身于填海工程。那座碼頭倒是十分氣派,維多利亞式的拱門和圓柱,頂部覆蓋鋼鐵,耗資20萬港元,建筑費(fèi)是當(dāng)時(shí)一般碼頭的10倍。僅從外觀考慮,它較之現(xiàn)在的皇后碼頭,應(yīng)該更具保留價(jià)值。然而,當(dāng)時(shí)并不見有人出聲“捍衛(wèi)”。
雖然不復(fù)舊觀,但皇后碼頭卻一直是英國女王及其御用代表的身份象征。歷屆港督就任,都會(huì)乘坐游艇在皇后碼頭登岸,在愛丁堡廣場檢閱三軍儀仗隊(duì)后,再到大會(huì)堂宣誓就職。1989年,查爾斯王儲和戴安娜王妃訪港時(shí),也是在皇后碼頭上的岸。
從海上來,經(jīng)海上去。歷屆港督告別儀式,也都在皇后碼頭登船離去。
不過,關(guān)于皇后碼頭見證香港回歸歷史時(shí)刻的說法,卻是個(gè)誤會(huì)。10年前的6月30日,查爾斯王儲和“末代港督”彭定康改在添馬艦基地登船離港——因?yàn)橐呀?jīng)沒有維系傳統(tǒng)的機(jī)會(huì)和必要了。所以,彭定康回首時(shí)的“著名”表情自然也與皇后碼頭無關(guān)。
除了那些罕有的大日子,皇后碼頭絕大部分時(shí)間是寂寞的。
在現(xiàn)世香港人的眼中,相隔百米的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有著截然不同的“身份”:前者是玩樂,后者是生活。
“那時(shí),如果大人帶著我們坐游艇出海玩兒,一定是從皇后碼頭上下船的。現(xiàn)在去皇后碼頭心里還是會(huì)很高興,看到碼頭就會(huì)覺得這是一個(gè)開心的日子。”香港著名傳媒人查小欣語。
在海底隧道和地鐵還沒開通的年代,每天數(shù)以萬計(jì)的市民要靠天星小輪來往于港島和九龍之間。渡輪是那時(sh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對多數(shù)人而言,皇后碼頭要拆了,難免有些失落。但比要拆掉天星碼頭,總少了些傷感。
以集體記憶之名
“集體記憶”一詞的反復(fù)出現(xiàn),是從拆除天星碼頭開始的。
期望在原址保留碼頭的人士說,“香港的現(xiàn)代歷史由海濱開始。然而2006年秋天,見證維港半世紀(jì)以來變遷的天星碼頭,難逃消失的命運(yùn)。這個(gè)碼頭可以供市民釣魚、坐船出海、拍拖時(shí)憑欄遠(yuǎn)眺夜景和拍攝結(jié)婚照,令此處累積了大量普羅大眾不可分割的集體回憶。”
少數(shù)人還出現(xiàn)在工地,試圖阻止工程進(jìn)行。
為了化解“天星事件”帶來的對立情緒,特區(qū)政府決定將集體回憶納入保護(hù)文物的考慮因素。
此后的發(fā)展,卻仿佛偏離了軌道,變得讓人困惑了。
文物保護(hù)人士說皇后碼頭是集體記憶,人力車是集體記憶,張國榮是集體記憶,飯店甚至說鴨掌也是集體記憶。當(dāng)所有東西都是時(shí),即所有東西都不是。
集體記憶,是法國哲學(xué)家與社會(huì)學(xué)家哈布瓦赫,為了與個(gè)體記憶區(qū)分而率先使用的。它的源頭是內(nèi)涵更加復(fù)雜的“集體意識”。根據(jù)《科林斯社會(huì)學(xué)辭典》解釋,集體意識就是社會(huì)里作為一種凝聚力量,民眾共有的信念和道德態(tài)度。那么,集體記憶就是社會(huì)大眾共有的記憶。
盡管明確了意義,但要將這樣一個(gè)社會(huì)學(xué)概念應(yīng)用到個(gè)別化的事件中,仍然會(huì)適應(yīng)不良。這里面有個(gè)最難解決的問題:集體是什么,或者說多少才稱得上集體。
“希望政府能修改有關(guān)的規(guī)劃,原址保留皇后碼頭,以及不再破壞屬于全港市民的維多利亞港、屬于全港市民的集體記憶。”總有人這樣說。
于是尷尬出現(xiàn)了。皇后碼頭背負(fù)的集體回憶,遠(yuǎn)遜天星碼頭。問市民對哪個(gè)碼頭有親切感,九成以上會(huì)答天星。乘游艇出海,更多人喜歡用尖沙嘴公眾碼頭。情侶談心,寧愿坐在愛丁堡廣場或大會(huì)堂花園。
“皇后碼頭我沒搭過,沒什么感情!”這應(yīng)該是排斥集體記憶的最直接表達(dá)了。
香港故事如何說下去
“香港拆得太多,歷史要靠實(shí)物講故事,香港的故事如何再說下去。”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語。
香港作家董啟章說得更明白:“歷史記憶因其為記憶,也似乎只要銘存于心,或者以仿制的替代物供人憑吊,就可以‘拋開過去的包袱,歷史于是變成了發(fā)展的障礙。可是,歷史作為賦予一個(gè)族群存在的意義的故事,并不是寫在書上的文字,它是由活生生的主觀記憶和客觀實(shí)物交織而成的。”
發(fā)展論者卻握有最難辯駁的論據(jù)。香港本來是個(gè)漁村,中環(huán)原本就是海,今天的香港就是一個(gè)“破舊立新”的故事。他們擔(dān)心,香港的基建步履維艱,任由鄰近地區(qū)的競爭對手大步追趕以至超前,本來的東方之珠會(huì)成為人老珠黃的一顆殘珠。
港府?dāng)?shù)據(jù)顯示,香港基本工程項(xiàng)目的開支,在2004/2005財(cái)政年度高峰期約250億港元,隨著迪斯尼樂園、后海灣干線、深圳灣公路大橋等大型工程陸續(xù)竣工,它直線下跌到今年預(yù)算的150億港元,是回歸以來的新低。眾多建筑工人都要去澳門開工,或者上大陸找生意。
面對保護(hù)歷史與發(fā)展的天然矛盾,一些人開始尋求折中的解決方法。港府提出在皇后碼頭原址附近“拆卸重組”的方案就是一例。可惜,結(jié)果還是批評者眾:將皇后碼頭重置在馬路中間,失去回憶意義,碼頭日后可能需要易名為“皇后涼亭”。
不論是原址重置碼頭,或是另覓地方重置,皇后碼頭都能幸運(yùn)地留下實(shí)物了。更多的東西在完成使命后只有消失一條路。那么何妨快樂告別?
“本店于2006年11月9日光榮結(jié)業(yè)。多謝各坊好友多年來的支持,祝生活愉快,身體健康!”皇后碼頭小吃店在歇業(yè)告示里這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