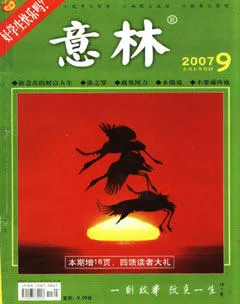其實這只需要一小步
張小失
明天,我一定能買一張機票飛向天涯海角;但是,明天,我不一定能抵達對門客廳的沙發。永遠有多遠?就有我到對門的客廳那么遠。
在這幢樓住了近兩年,但是,即使我的對門,也令我感到陌生。對此我感到抱歉,他們似乎沒有任何興趣認識我;而像我這樣的人,似乎也不指望認識任何人。
當然,如果很多年后的一天下午,作為老翁的我,在城市的公園里遇見另一位老翁,并產生一次愉快的交談,我會期望他年輕的時候曾與我住過對門,這樣,也不枉過去的那一點緣分。如果這世界的確有緣分存在,那不是在公園里的偶遇,而是偶遇過去的對門。如今的對門使我充滿了想象力。在如此近的距離中,存在著如此神秘的人物,的確是件值得注意的事。也許,在對門眼中,我也是個外星人。
那對小夫妻早就搬走了,招呼也沒打一個;接著來了個小伙子,3個月后不知所終;如今對門的中年夫婦是半年前住進來的,至今沒見過他們全貌。大家都很忙,對門的存在就像一種點綴,供休閑時隨便瞟一眼。對門的價值,有時甚至比不上辦公室里的那只鞋柜。
有一天,太太來這里探望我,問起對門是干什么的,我說是開門并關門的。太太問,然后呢?我說,然后他們再開門再關門。對于對門,我的了解大抵如此。因為常常在深夜聽見“轟”的一聲。這幢樓安的好像全部是防盜門,因此,無論開門、關門,聲音都很憤怒,充滿了警告。
又一天傍晚,我站在陽臺,看見了對門的陽臺。我一邊抽煙,一邊幻想:也許對門的人會上陽臺來與我對視一次。果然,他出現了。他舉著曬衣竿將褲衩挑上鐵絲,然后轉身回屋,再也沒動靜。這是個夏天的傍晚,空氣中滿是灰塵和燥熱。看著對面陽臺安裝的鐵欄桿,以及我自己陽臺上的鐵欄桿,我忽然意識到:兩個囚犯是不需要對視的,除非他們想合謀逃出牢籠。
事情基本上就是這樣了。我可以產生很多幻想,但不可以產生很多希望。或許,對門對我的感覺也一樣?而且,大家基本上也都習慣了。
阿姆斯特朗已經從月球回來好多年了,他說他代表人類邁出了一大步;而我、我們,甚至還沒有抵達對門,其實這只需要一小步。
(平珠摘自《洛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