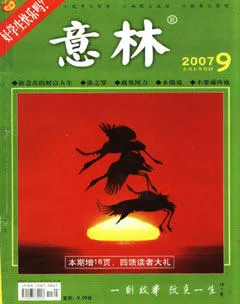門面
陳世旭
到波士頓的第一個念頭便是去看哈佛大學,但因為是晚上,只能等天亮。一早起來,啃著面包上車。
雨雪霏霏,天空和街道都灰蒙蒙陰沉沉的。車子在一條窄小的鵝卵石路上停下來,兩邊是一些舊房子和低矮的門面,車子停靠的位置,臨著一扇極普通的鐵柵門,門兩邊的紅磚垛已經灰黑,里邊貼著一間在國內常見的簡易房。我以為車子出了故障,卻聽說:“到了。”也就是哈佛大學到了。那扇門里就是,陪同說,我們現在去正門,一會從這里出來。
原來這是偏門。即便如此,也足以讓我驚訝:畢竟是讓世界各國的求知者那么向往的哈佛大學啊。這樣的偏門,好像還不如我所在的那個無足輕重的社團多年沒有維修的偏門呢。可是拐個彎,到了正門,我的感覺更不止是驚訝,完全就是疑惑了。以為陪同是敷衍塞責,把我們帶到了另一扇偏門。結果人家倒很驚訝,反問:這就是正門呀,怎么會不是呢?
依舊是已經灰黑的紅磚垛。依舊是黑色的鐵柵門,只是比先前的那個偏門稍寬,紅磚垛上嵌了刻著校名的石頭。進門便是穿過樓群的林蔭道,遠遠的盡頭,是那座由一個學生做模特的約翰。哈佛的著名雕塑。我不能不相信,這就是哈佛大學的大門。
我的驚訝和疑惑,源于我對國內大學校門的見聞。我有一次因為偶然的機會路過一所省級大學的新校區,被其孤零零地突兀屹立于一片廣闊曠野上的校門抓住了視線。這幾年教育產業化,大學擴招,收費猛增,銀行也把大學當作了投資熱點,有求必應。同行的人中有個知情的介紹說,該校為建新校區,一口氣貸款二十個億。規劃尚未全部完成,但這座宏偉堂皇、傲然雄視、耗資千余萬的校門,及其所表現出的主事者的手筆與氣魄,已令無數觀者乍舌驚嘆。
我因為所受教育的主要部分是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對日新月異的教育現狀幾乎沒有發言權,我能做的只是事實的對比:
資料表明,哈佛大學自1636年在此馬薩諸塞州查爾斯河畔建立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學府———哈佛學院開始,370年來,就是從這扇簡樸的校門,走出了無數的政治家、科學家和文學家。其中有美國獨立戰爭以來幾乎所有的革命先驅;有7位美國總統、40位諾貝爾獎得主和30位普利策獎獲獎者;微軟、IBM……一個個商業神話的締造者;溝通中美關系的基辛格,奠基中國近代人文和自然學科的林語堂、竺可楨、梁實秋、梁思成。美國“總經理搖籃”、美國政府思想庫,就是這樣一扇門。在這扇門下進出的許多人的一舉一動決定著美國的政治走向與經濟命脈,乃至世界無數驚心動魄的故事的開始和結束。
而國內那所大學,盡管矗立起了足以令哈佛慚愧的新校門,但如何把真正的教育人才引入這扇門依然是最大的苦惱。與此同時,那扇門也依然沒有阻止住現有可用師資的流失。
這些年來,國內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其中包括那所大學的負責人,參觀過哈佛大學的,肯定不在少數。他們應該都摸過那個已經被無數人摸得錚亮的哈佛先生的銅皮鞋,也都知道當了20年哈佛校長的科南特說的“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質量”;知道“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的哈佛校訓;知道這些文字所昭示的立校興學的宗旨:求是崇真;知道哈佛大學在上世紀最后十年平均每年得到十億美元的社會捐贈,卻只是一味致力于世界第一流學府的學術發展而沒有重建校門。
(白偉明摘自《今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