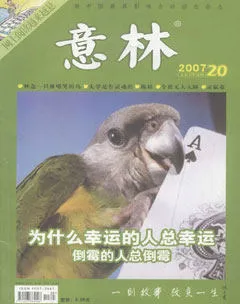別“太早說再見”
回首人生,我根本不認為腎臟會給我的生命帶來什么隱患。它們默默地工作,從不吹噓自己厲害。但是幾年前。我開始注意我的腎了。那時我在印第安納州試圖排出一塊腎結石。那次經歷我永生難忘。想想吧,泰坦尼克號要過小溝渠!我相信,一個排石的人會愿意用所有財產換一支止痛針。
我的印第安納州大劫結束以后,有四張結石的照片流傳出來。這塊石頭很快舉世聞名,連美國地質研究所都給我來信了。他們可是研究月球的啊!
要解決問題時,總能想出數量驚人的應對之策。我的第一個念頭。和大家一樣。就是做腎臟移植手術。但是等腎磨人啊!大夫說就算我等到了,我的年紀和血壓也不允許我做這個手術了。而且。手術后的藥物也有風險。我的兒媳婦提出要捐腎給我。我當然拒絕了。帶著自己兒媳婦的腎到處晃蕩多詭異!
大夫告訴我,透析已經迫在眉睫。我拒絕了。
然而,80歲生日剛過幾周,我的右腳就開始劇烈地疼痛起來。醫生說我的動脈里有血塊,影響了血液循環。他們想為我化開血塊。重建血流。但是他們失敗了。我就要失去我的右腳和小腿了。這讓我很不高興。醫生說如果我不做切除手術,壞死癥會害死我,那個聽起來更惡心。我必須做透析來配合切除手術,真是晦氣。我煩躁、憤怒、絕望。但是,我同意開始透析,趕緊把小腿和腳切除掉。手術后。我也不再拒絕透析。反正愛我的人都不同意我安樂死。雖然我以為那才是上計。我一共透了12次,發覺自己實在無法再忍受。“就這么著吧。”我說,“我根本看不見透析能給我什么未來,我再也不想做了!”就在那時我產生了住在收容所的念頭。我有了新的選擇。
醫生提醒我:“這是你選的。”他們斷言在停止透析之后,我只能活3周。
2006年2月7日,我在華盛頓的收容所得到了一席之地。那里位于一條繁華的街道,我告訴訪客們,死很容易,但找車位沒門兒。
我在收容所的空間很大,我把它稱為我的沙龍。白天我就在那里會見朋友,看電視,讀書,打瞌睡。晚上。我回到臥室。收容所里也就我舍得離開床鋪。
長椅成為我做心理治療的地方。我的朋友會從我的病情談起,然后馬上轉到他們自己的問題。我一小時才收75美元。畢竟。在收容所里沒什么心情賺錢。
在收容所待了5個月之后,我發現我并沒做好立即上天堂的準備。于是我回到了位于瑪莎葡萄園的家里。以3周為限的死亡之旅變成了5個月的吃喝笑談,在公眾的關注下,國家臨終關懷計劃基金會宣布我成為他們的年度代言人。
說真的,我在收容所里度過了如此美好的時光,我一定會想念這段日子的。我從來都不知道走向死亡的路程也可以充滿著巨大的歡樂。
在生命中的某一時刻——也就是現在——我有兩個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我正在做什么?我要去哪里?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非常自戀——我生而為了人們的笑容。第二個問題就難回答了——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沒有人知道答案。
注:包可華,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普利策獎得主。80歲時因腎病截肢。他拒絕透析治療,搬進了臨終關懷療養所(被他嘲為“收容所”)。被醫生診斷為只剩下3周生命的他,提前錄制了一段錄像“你好,我是包可華。我剛剛去世……”但是,他并沒有“按時”赴死,于是有了這本書:《太早說再見》。在“堅持”了約一年之后,他于2007年1月17日逝世。
江浸月摘自《太早說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