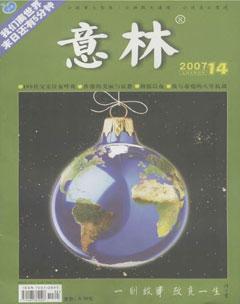花落兩邊開
秋日莫莫
她和他住在—個胡同,兩小無猜,青梅竹馬。她比他大兩歲,自然上學要比他高兩個年級。升高中時,為了她讀書便利,便舉家遷移。她死活不依,卻難奈家中的決定。穿過那片挺拔的白樺樹林,他駐足,目光堅毅地對她說:我很快會來。她眼噙淚花點點頭,默默而去。
他果然沒有食言,不僅如此,他還申請了跳級,學校鑒于他成績優秀,態度懇切,批準了。就這樣他們分在同一個班,且做了同桌。除了在宿舍,絕大部分時間他們是在一起的。上課、自習、泡圖書館、晨跑、散步,一如以往的形影不離。
人們常說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一次意外,她出了車禍,在醫院里呆了一年。待出院,他已考到上海復旦。臨行,她去送他。這次,換了她在轟隆隆的火車邊對他說:我很快會來。他拉著她的手狠狠點頭,依依不舍地上了已在開動的火車。
上天常愛捉弄人,她的成績盡管是一直優異的,可是歷經那一次車禍后,體質變得異常差。在遇到大型考試時,神經稍一緊張就會骨頭發軟,站立不穩甚至是昏迷休克。醫生說這是車禍留下的后遺癥,建議她讀一般大學則可。家人知道她的病,勸她,她不肯。整整讀了五個高三:武大錄了三次,浙大錄了一次,她都沒去。嘲笑和不解鋪天蓋地地向她涌來,連家人都責備她,他也勸她了,她仍執著。
最后一次終于盼到花開。就這樣,她到了他的大學,他已讀研。當她從火車下來被他緊緊擁在懷里時,兩人都情不自禁地流淚了。她是開心的,那些逝去的美麗年華,所有的努力和忍耐,在這一刻都得到了補償。她覺得值了,認為這樣就可以相擁一生。
她畢業后,兩人在同一家大醫院工作,日子如絲綢般光滑而舒暢地流過,甜美溫暖至極。兩人常常陶醉其間,十指相扣構想著幸福的未來。
可惜這并不是屬于他們的美麗結局。她的“后遺癥”頻頻復發,作為醫生的他們很快就明白這不是個好兆頭。她日漸消瘦,他日漸憔悴,焦急。常常抓著自己的頭發哭喊,怨恨蒼天如此不公。
他的母親趕到醫院,趁他不在,用手指頂著她的額頭罵:害人精,自私鬼,拖累有大好前程的他,不是愛他是害他……她那深深凹下的眼睛迅速地凸起來,卻百口莫辯。在他母親的眼淚和哭訴中她投降了,也認可了他母親的話———既然不能給他幸福,那不如早些放手。
她是如此愛他。很快出了院,不知去向。
待再見她時,已是他人婦。他當上了一家大醫院的院長,在腦科上造詣頗高,享譽國內外醫學界。只有他知道這么多年潛心研究,全是為了她。她聽了這些,并不動容,淡然而笑說:你現在不是有個很好的家么。他那熾熱的目光有些黯淡下來。是啊!一轉身,都已人到中年,各有一個家了,已任不得年輕的輕狂,遐想。聊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各自散去。她坐在車里,待他走遠,這才抬起頭來,拂起長長的劉海兒,那眼里閃亮似啟明星一般,他不曾知道她的眼睛是閃著火苗的。
此后,她成了他的紅顏知己,他亦是她的藍顏知己。生活仍在繼續。直到他的母親去世,彌留間告訴他她當年離去的原因。他不怪母親,但內心震痛,血往上涌。他決定找回她,不管花多大的代價。
三月的揚州路,櫻花的花瓣帶著芬芳飄落滿地。他驅車急馳前往,到門口,見她正在教孩子念詩,神情如往昔那般從容,安然,淡定。瞬時,他怔住了。悄然停駐良久,慢慢地驅車而回,一朵花正好掉到前窗來,分成兩瓣,朝兩邊散落開去。下車,看著兩個完好的半邊花瓣。他若有所悟,隨后釋然了。
這世界上有一種愛,本該是一個整體,可被世事如花般給分開,成為另外的兩個整體,并且各自很好地開放,那么為何不去成全這種好呢?不是不愛,而是愛太深,不忍再讓其破碎。
(張鳳祥摘自《參花·愛情故事》2007年6月圖/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