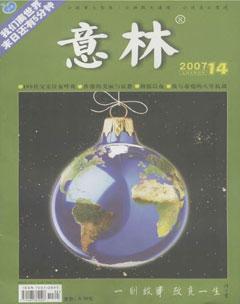愛比屋檐低
郭姜燕
當時,他與她已經有了四個女兒,她卻主動放走了他。
他是上海的大學生,下放在她所在的江心小島,她是島上惟一的高中生,村小的代課老師兼掃盲班的老師。他來了之后,經常幫她,成了她的“老師”,愛情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結婚后,他成了村里第一個釣魚的人。其實,沿河的人家都在河堤邊架著漁網,想吃魚,網一撒就有了,可他總愛在河邊,執著一支漁竿。她就看著他笑,由著他釣,飯熟了也只低低地輕喚他,生怕驚跑了他的魚兒。
他被調回上海之前,徹夜流著淚,她卻無憂無慮的樣子,說,回去吧,安頓好了來接我們,然后打起了呼嚕,睡得很熟的樣子。他記得,她是不打呼嚕的。
他回到上海后,情況不如想得那樣好,他提出過接她們過去,她拒絕了,說先顧好自己。
后來,他結婚了。自然,先與她離了婚,女兒們也都跟著她。
二十多年一晃過去了,女兒們一個個從她身邊飛走了。她依然獨自一人,沿河住著。
她不會釣魚,卻喜歡在河邊坐著。呆呆地盯著水,那水里的魚蝦快活地游著,鬧著,慢慢地,她也快活起來,似乎明白了他為什么那么喜歡釣魚了。
都說她傻。
她是村里最俊的女子,卻守著活寡。他離開了再婚了,她卻始終不肯再嫁。最困難的時候她賣過血,和男人一樣去建筑工地抬過磚,直到代課教師轉正,她的日子才稍稍輕松一點,可生活已偷走了她的青春,一點不剩。
二十多年,他居然沒回來看過她們一次。連最大的女兒都記不清他的模樣了,恨恨地跟妹妹們說,我們的爸爸早死了,要記住,我們只有媽媽。
誰也沒有料到,當她老了的時候,他卻回來了。
送他回來的是他后來的兒子。兒子有些歉意地告訴她,他退休不久就開始迷糊了,老年癡呆。他不認識兒子,不記得自己是誰,出了門就不清楚回家的路。可是,卻記得她,對著后來的妻子的遺像,叫的卻是她的名字,然后鬧著要找她,偷偷跑出門,不是鄰居發現得及時,可能早就跑丟了。
他對著她傻笑,很顯然,他不認識面前的滿頭銀發的老太太。她叫他的名字,他的眼中閃過一絲亮光。他竟然也喊出了她的名字,卻依然傻傻的。她知道,他記憶中的她,不是現在的她。
她還是把他留下了。
她幫他剃去了蓬亂的胡子,她帶著他在村子里散步,告訴他哪些是過去的朋友,哪些人曾經幫助過她和女兒,叫他謝謝他們,他很順從地笑著。她陪著他坐在河邊,看水邊的蘆葦搖曳,看水中的魚兒嬉鬧,他會顯得特別安靜。
她牽著他的手在老屋中進進出出,老屋還是那么低矮,他竟然不用她提醒就像幾十年前那樣把頭低下來了。她干涸了幾十年的心一下子浸潤了,多少年的眼淚似乎一下子就涌了出來,她想把這個男人摟在懷里,緊緊的,再也不分開。
奇跡般的,他的舉動越來越像那個她熟悉的他。沒有藥,沒有醫生,有的只是她對他的喁喁細語和溫柔體貼。
看著他對她依賴的神情,看著心目中一直強悍無比的她溫柔如水的樣子,女兒們知道,這個曾經給她們帶來生命和傷害的爸爸,是母親失而復得的愛情。她們咽下了本來想說的很多話,只是和母親一起,收拾著屋子,然后,圍坐在兩個老人身邊,享受著遲到的完整的家的感覺。
女兒們明白了,母親堅守著老屋,那是在堅守自己的愛情啊!
(龍沙冷月摘自《時代姐妹》2007年第5期圖/叢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