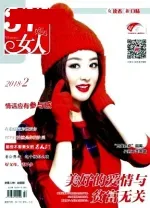大孝至愛
周士德
2006年11月28日,在連續幾日的雨雪寒冷天氣后,是一個難得的艷陽天。
那天下午,謝粉香剛剛從焦作回到滑縣半坡店鄉車村家中,就被熱情的村民圍了起來。滑縣縣委書記劉國連等領導來到她家,并帶去了棉被、食品、現金等。
“不但謝延信是大家學習的榜樣,你們全家都值得大家學習。我們為你們感到驕傲和自豪。”劉國連握著謝粉香的手,激動地說。
——謝延信、謝粉香是誰?他們為什么會如此引人注目?
這還得從34年前說起……
許下諾言
1973年4月16日,21歲的滑縣半坡店鄉車村青年劉延信與同村姑娘謝蘭娥喜結連理。第二年7月,謝蘭娥生下一個可愛的女兒,取名劉變英。女兒的出生給初為人父、人母的劉延信和謝蘭娥帶來了無盡歡樂。
然而,快樂的時光僅僅延續了40天。40天后,謝蘭娥因患產后風,命懸一線。臨終前,她含淚拉著丈夫的手,一遍遍叮囑:“延信,我怕是不中了。你要照顧好咱爹娘和我那苦命的傻弟弟。以后再找人家,要對咱閨女好……”
望著彌留之際的妻子,再看看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女兒,劉延信淚流滿面。他緊緊握著妻子的手說:“你爹娘也是俺的親爹娘,你弟就是俺的親弟,你放心吧。”
“放心”二字,說來簡單。劉延信的岳父岳母膝下只有一兒一女,兒子先天呆傻,生活不能自理;岳母體弱多病,生活需要照顧。望著棺木中的妻子,看著悲痛欲絕的岳父岳母,還有跑來跑去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的傻內弟,劉延信做出了他這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
他“撲嗵”一聲跪倒在岳父岳母面前,磕了三個響頭:“爹、娘,蘭娥不在了,從今以后,俺就是你們的親兒子!你們放心,謝家今后的生活俺來管,俺替蘭娥為你們二老養老送終!”
男兒膝下有黃金。劉延信這一跪,跪出的是男子漢字字千鈞的承諾;跪出了一個大孝至愛、感天動地的謝延信……
做謝家的親兒子
一句“蘭娥不在,俺就是你們的親兒子”,讓劉延信承擔起了謝家的全部責任。
謝蘭娥去世時,劉延信才22歲。不光是岳父岳母心中惴惴不安,鄉里鄉親也都在紛紛猜測:延信再婚后就會有自己的小家庭,那么謝家多病的二老、癡傻的內弟誰來照顧?沒有了延信,這個家誰來管?
眾人的疑慮,劉延信看在眼里,記在心上。他做出了一個誰都沒有想到的決定——改姓。
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一個人,特別是一個男人的姓氏,就是家庭宗族的代名詞。在農村,改姓是個了不起的大事。為了這事,劉延信把自家“延”字輩的兄長都叫在一起商量,大多數兄長都不同意這件事。看著眾位兄長,劉延信的目光中透著誠懇和堅定,“蘭娥去世后,大家都在想,我什么時候會再婚,再婚后是不是就不管兩位老人了。我肯定會侍奉老人直到他們百年的,既然有這個決心,就不如把姓改了,讓大家放心。”說到這里,這個鐵錚錚的漢子眼中閃著淚花。最后,原來最反對這件事的劉家堂兄,親自幫延信辦了改姓手續。從此,謝家多了一口人,多了一個“兒子”。
料理完謝蘭娥的后事,謝延信的岳父帶著悲傷一個人去了170公里外的焦作煤礦上班。謝延信先是把岳母和內弟都接到家里安頓下來,兩個月后,為了能照顧到岳父,他又帶著女兒和岳母、內弟一起來到焦作,在岳父上班的朱村礦附近一個磚瓦窯場打起了短工。岳父每天要上班,岳母患有肺氣腫、胃潰瘍,內弟生活不能自理……謝延信每天洗衣做飯,刷鍋洗碗,陪兩位老人聊天,喂傻弟弟吃飯,儼然成了謝家的頂梁柱。
對自小失去母愛的女兒,謝延信疼愛有加。可來到焦作后,他常常是顧了老人顧不了孩子,顧了孩子顧不了老人。最后,他一咬牙,把女兒送回老家,交給年邁的母親撫養。為了能讓孫女吃上奶,延信的母親從親戚家借了一只羊,買了煤油爐,每天擠了羊奶,加熱后喂給孩子。
女兒離開后,謝延信一邊照料家,一邊抽空到窯場出磚,到建筑工地提泥,再苦再累,只要能多掙點錢,他都愿意干。那時,他去地里挖過野菜,去菜市場撿過白菜葉,還在住所旁邊開了片荒地,種了一片油菜。“這東西真不錯,嫩的時候可以剔著吃,再大些時候可以涼拌著吃,長老了可以炒著吃,開花結籽了還可以榨油……”一片油菜,為謝延信省下了不少買菜錢。
1975年春天,謝延信的三哥劉延勝來到焦作看望弟弟。“雖說是城市,可他們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了。”說起當年去焦作看弟弟的情景,劉延勝記憶猶新。當時,謝延信在一個磚瓦廠做工,用辛苦掙來的錢給岳父岳母買水果,自己卻長期吃自家腌制的咸菜。“你才二十多歲,只顧在這兒伺候他們,以后咋辦?”劉延勝掉著眼淚問謝延信。
“我知道你們是為我考慮,可這邊的情況你也看到了,我一走,這個家怎么辦?”謝延信含淚送走三哥,堅持留在了岳父岳母身邊。
1979年春天,謝延信的岳父在礦上的集體宿舍里因中風昏迷不醒,被工友送到醫院。謝延信接到電報后,急匆匆趕到醫院急診室。看著病床上還沒過危險期的岳父,他心中無限悲傷——以前,雖然日子過得艱難,可還有岳父可以依靠;現在,岳父也倒下了,以后家里的日子該怎么過?
謝延信整日整夜守護在病床前,躺在床上的那位老人,在他心目中已經和自己的生身父親沒有什么兩樣。也許是他的真誠感動了上蒼,也許是老人家放不下這個苦難重重的家,在與死神搏斗了七天七夜后,老人從昏迷中蘇醒過來,然而,卻永遠失去了站立的能力。
床前盡孝17載
謝延信面對的是怎樣一個家啊——家中一病、一癱、一傻,沒有一個不需要照料。
岳父躺在床上,一躺就是17年。而在這17年里,老人從沒有生過褥瘡,也從沒有穿過一件濕衣裳。謝延信每天用熱水給老人燙腳、按摩,還照偏方挖了許多毛草根給老人熬藥。在謝延信的照料下,岳父竟然奇跡般地能扶著凳子慢慢挪動了。
1989年春,岳父先后患肝硬化、癲癇、咽炎等病癥,住進了焦作礦務局大醫院。別的老人住院大都兒女輪流伺候,可謝延信一個人在醫院里日夜守著岳父,困了就趴在床沿上打個盹兒,實在頂不住,就和衣躺在病房的水泥地板上睡一會兒。
“老人家,您有這么個孝順兒子,是您老的福分啊。”看到謝延信日夜守候床前,忙前跑后,一名護士對病榻上的老人感嘆道。
“閨女,你不知道,他可是我女婿呀。”一句話出口,謝延信的岳父已是老淚縱橫。
一片孝心沒能阻止死神的腳步。1996年8月28日下午,已經昏迷了兩天兩夜的老人突然睜開眼睛,盯著謝延信,嘴張了張卻發不出聲音。
“爹,您放心,只要我有一口飯吃,就不會讓娘和弟弟餓著。娘百年后,讓弟弟跟著我,決不讓弟弟受一點委屈!”謝延信知道岳父的心事,把岳父的頭放到自己懷里,動情地說。
聽了女婿的話,老人艱難地點了點頭,兩行熱淚從深陷的眼窩里流出來,安然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所有的一切,鄉親們都看在眼里。謝家的鄰居呂國成抹著眼淚說:“咱們土話常講,床前百日無孝子。人老了以后,兒女能伺候你100天都不容易,可謝延信伺候謝家的老人,伺候了幾十年哪……”
兩個人的肩膀更有力
謝粉香走進謝延信的世界,是在1983年9月。
妻子去世后,很多人都曾給謝延信介紹過對象。他惟一的條件就是不能違背自己當年的承諾,不能丟下風雨飄搖的謝家。
打動謝粉香的,正是謝延信的忠厚與善良,也正是他這片至誠至信的孝心。“我覺得,他對他的岳父岳母那么好,我嫁給他,他一定也會對我好。”就這樣,明知道跟謝延信生活在一起會吃很多苦頭,謝粉香還是走上了這條艱難的道路。
再婚后,他們有了一個女兒。之后,謝延信在焦作煤礦伺候岳父岳母和傻內弟,謝粉香在老家替他撫養女兒、侍奉雙親、耕種田地,每隔一段時間就到礦上為丈夫的岳父岳母一家拆洗被褥。“前些年,他在焦作,我和孩子們在家,甭提日子有多難了……”
日子再難也要過,謝粉香帶著自己與前夫的一兒一女,帶著謝延信的女兒劉變英,還有自己與謝延信的女兒,一家5口人,用莊稼地每年的微薄收入和大兒子外出打工掙的血汗錢,硬是拆掉了舊房,一磚一瓦建起了自家的小樓房。
兩個人的肩膀總比一個人更有力。謝粉香的出現,不僅給謝延信的生命和信念注入了一縷曙光,也給謝家老小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
一家好人
謝延信患高血壓病是從1990年開始的。當時醫生就囑咐他安心休養,可這個家的狀況讓他怎么休養呢?聽一位老中醫說醋泡花生能降血壓,為了省錢,這個偏方他一吃就是13年,沒有去醫院買過一片藥。
2003年,謝延信因腦梗塞住院,謝粉香立即放下家中一應事務,從滑縣老家趕到焦作,在照看丈夫的同時,像對待親媽和親弟一樣,照顧著謝延信的岳母與內弟。
一年時間,謝延信三次住院,后來雖然轉危為安,卻落下了嚴重后遺癥,行動遲緩,記憶力衰退,語言表達不清。從此,除了秋收種麥的農忙時節,謝粉香大部分時間都留在了焦作,將這個四口之家的重擔挪到了自己肩上。
“先前是公公在焦作伺候老人,婆婆在家留守,現在婆婆又去了焦作,輪到我在家留守了。”謝延信的兒媳馬海霞這樣說。
2003年4月,馬海霞的兒子還沒有滿月,因為公公生病,婆婆不得不先去焦作照顧公公。當時正趕上收小麥,姐妹們也都在外地,婆婆一走,她只好下床給在地里收麥的丈夫做飯,給孩子洗衣服、洗尿布,因為產后身體虛弱,一天下來頭暈眼花。“這還不算什么。今年秋收時候,丈夫在外打工沒回來,婆婆在焦作伺候生病的公公,家里13畝玉米都是我一個人收的。我把孩子放到地頭上,就鉆進了一人多深的莊稼地里。后來,3歲的兒子哭著跑進玉米地找我,臉被玉米葉子劃出了血……”說到這里,馬海霞的眼淚掉了下來。
常言說: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了解這個家庭的人都說,這一家子,好人都聚在一起了。
34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這個特殊的家庭和家里那份質樸但卻深沉的大愛,感動了越來越多的人。由于多次腦梗塞造成的記憶力衰退,這34年中的許多事情,謝延信都已經記不清楚了。34年前的一個選擇,讓他嘗盡世間艱難與困苦;34年中信守一個承諾,讓他擁有了與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遜色的父母情、夫妻愛。
提起當年的選擇,謝延信的話語卻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兒女伺候老人是天經地義。事情重新來過,我也還是得那么做……
(摘自《殷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