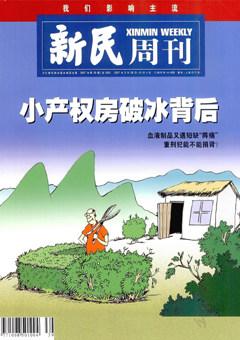城市群發展“重”在功能培育
朱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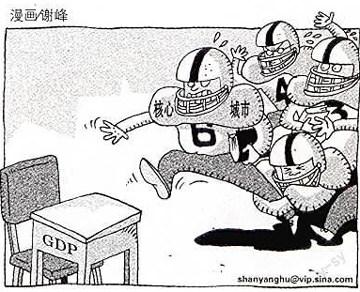
一段時期以來,傳媒對世界城市群的報道趨熱,一些研究城市經濟的學者對于長三角城市群的現狀和前景也多有議論?在此,我首先想強調的是,迄今世界上尚無一嚴肅而權威的機構(包括法國著名學者簡·戈特曼本人在內)曾為世界城市群排過座次,長三角城市帶只是戈特曼很久以前一篇著作中所舉的例子罷了,或許只是個純地理學概念?故此,目前探討長三角城市群發展時不能過度渲染“第六城市圈(群)”,需要的是破解問題,多干些實事?
說到長三角城市群,我想先要看清當今世界已經發生這樣的趨勢:國家與國家的經濟關系,已經逐步讓位于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經濟關系,城市間的經濟網絡開始主宰全球經濟命脈,世界性的節點城市成為在空間權力上超越國家的實體,以大都市圈(群)為特征的全球城市體系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而我國的若干都市群,正在成為決定國家經濟未來發展走勢的重要力量,其中尤以16個城市組成的長三角城市群為最,它以10.95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和8161.01萬人口,即以占全國1.14%的土地和6.32%的人口創造了占全國1/5以上GDP?
城市化作為城市群形成的初級形式,其歷程極其漫長和曲折?長三角的城市化發展經歷了小城鎮建設?中小城市建設?大城市發展和城市群形成等四個階段,階段之間在時序上有所交錯,無法截然分割?從長三角城市群發展階段的演化判斷,城市群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其進程取決于城市發展戰略和管理制度的創新程度,它的發育與國際產業轉移力度相聯系,其互動效率與核心城市輻射強度和引領地位相關?有鑒于此,當下要推動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我認為“重”在功能的培育和完善?其對策是:
首先,應重視長三角城市群發展過程中共同主體的培育?在長三角城市群互動中,多個城市主體在行為上的相互合作,實際是一種協同(synergy)過程?協同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任何一種有目的性的活動都可以通過協同方式進行?計算和驗證表明,當各個單元主體處于各自為政的自然狀態下,其協同效率的最大值不會超過44%?要提高協同效率,必須培育一個協同主體進行有效組織?根據國際成功的經驗,這個協同主體的權威性標志有二:一是具有投資和規劃的決策權;二是具有法人資格的實體?與之相對照,可采用類似的兩個方案:方案之一是國務院批準設立長三角經濟特別行政區(或稱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方案之二是國務院下設“長三角經濟管理局”?設立上述機構的目標是,有利于培育長三角地區統一的利益主體?決策主體?規劃主體和投資主體?
其次,應從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角度強化城際內在聯系?城際之間內在聯系,主要體現在經濟關系之上,其關系的主體是企業?現代企業發展戰略演化的趨勢,正在促使企業的資源從傳統的垂直整合走向現代的虛擬整合?這種資源整合的新趨勢,適應了全球海外專業市場的發育,有利于從供應鏈關系構建的角度,推動城際之間的產業集群,進而強化企業的規模效應?其過程實際上是企業跨城際的一種資產重組,也是企業生產流程的分解與重組,它能將城市群的內在聯系固化,即經濟化?市場化和規范化?這一進程的操作平臺,可以充分利用1997年7月21日成立于上海的全國第一家區域性的產權交易市場——長江流域產權交易共同市場?作為配套,建議中央優化企業現行的所得稅體制,完善共享稅制度;建立長三角地區聯合開發銀行,突破傳統行政區劃對企業跨區域重組時所獲貸款的制約;健全法律體系,盡快完善企業產權交易規則?資產重組是企業重建功能布局的過程,其形式有三:一是遵循企業供應鏈管理關系,形成有效?合理的跨越城際的空間布局體系;二是借助國內大中型企業進入跨區域發展階段?相繼調整功能布局的時機,在核心城市上海與原創地之間形成垂直分工體系;三是隨著城市功能的轉換,上海企業向內地延伸生產鏈,重新構建城際之間空間的互動體系?
其三,應加快提升核心城市上海的功能地位?長三角地區城市之間功能雷同?分工欠合理?競爭過度的主因是核心城市上海的功能轉換遲緩?中央政府賦予上海城市功能的定位對城市發展模式提出了高要求,即上海將要從存量經濟中心地位的加工功能為主,轉向流量經濟中心地位的服務功能為主?這一切換,必然會對城市各種要素的流動速度?與此相配套服務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其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提出了全新的標準?但由于多種原因,這種轉換的進度不盡如人意?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例,這是國際大都市指標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尺度,也是上海城市功能轉換力度的重要標尺?如紐約為86.7%,倫敦為85%,東京為72.7%,北京也已接近70%,而上海只占50%左右?由于核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產業之間的資本結構和技術結構缺乏足夠的差異性空間,制約了核心城市的輻射能力,導致城市群之間的產業關聯出現了“外高內低”的不正常狀況,即與海外企業的關聯度高于對內企業的關聯度?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區域規劃專家咨詢組成員,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