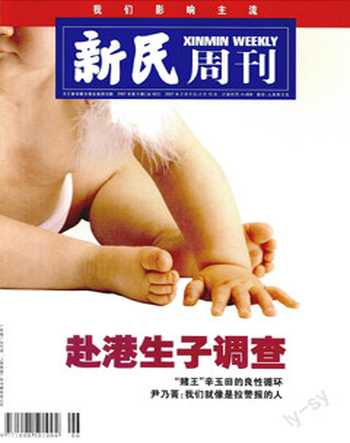跨國企業眼中的公益事業
張 靜

如果我們做善事的動機不夠純粹,事情不但做不好、做不長久,不良的動機也會被大家識破。
歐萊雅中國的副總裁蘭珍珍總是時尚界的話題人物。她在上海有棟與柯靈比鄰而居的小洋房,掛著趙無極送的畫作,喜歡著一襲絲絨旗袍、品上等滇紅、聽意大利歌劇。2003年與洪晃、孫莉聯袂推出自傳"激情女性三部曲"。39歲時欣然迎接小生命的到來,但她與相伴多年的法國情人都覺得結婚對于他們已經不重要。
近日蘭珍珍在北京接受了《新民周刊》的專訪。這次不談私密生活,而是她倍受矚目的另一面:公益事業。
在1月28日的公益盛典---2006公益中國年度評選頒獎晚會上,作為領獎中唯一的女性和跨國企業的代表,當主持人宣布進行媒體提問的時候,一開始幾乎所有的焦點都給了她。
回應作秀
新民周刊:在公益中國的新聞發布會上,武漢慈德通和的董事長許路加談到:"許多人說我們有錢,拿一些出來搞公益,純粹就是在作秀!"他的不滿得到了在場企業家的共鳴。你怎么看待來自于公眾的質疑?
蘭珍珍: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想做什么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如果我們做善事的動機不夠純粹,事情不但做不好、做不長久,不良的動機也會被大家識破。我認為公益和商業一定要分得相當清楚,不讓它們有任何牽連。
新民周刊:歐萊雅中國將負責公益事業的"對外交流及公共事業部"與品牌推廣部完全分開,這種做法在外資企業中是否為一種普遍模式?
蘭珍珍:我想并不多。雖然很多外企都在持續性地、有計劃地開展慈善、公益活動,但很多企業還是將公益事業包含在品牌推廣里面做。你將不得不朝著一個商業的角度去考慮任何一個活動,意圖就不純正了。
我覺得如果真心去付出,結果往往會比把商業目的放在第一位的效果來得更好。我們十多年來帶著這樣的心態去做我們的公益事業,起初很多投資根本沒有希望得到回報,但從最終來看,社會責任實際也是企業的一種競爭力。不是說增加了多少銷售量,而是顧客、員工、所有的客戶、政府對于你公司的敬意和好感。那個時候你就真的不要來跟我談銷售量是增了30%還是50%,我完全可以說:"歐萊雅的形象如此之好,銷售居然還沒有達到30%的增長?"
新民周刊:歐萊雅中國的公益之旅已有10年歷程,一開始就如此"激進"嗎?
蘭珍珍:歐萊雅公司剛進入中國,已經重點考慮要投入一些公益企業。第一件事是贊助了一個中法文化交流活動,1998年又贊助了全球華裔籍最大的抽象派大師趙無極"繪畫六十年回顧展"。當時請來了老先生早年在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任教時的幾位學生。他老淚縱橫,走上臺去與每一個學生握手,半個世紀的滄桑感慨盡在其中。那一夜趙老先生非常開心,80多歲的人了還和我們年輕人一起蹦迪,大聲歡笑。
這些活動在最初更多地帶有企業宣傳的色彩,但是我們沒有局限于宣傳活動本身那些約定俗成,在其中加入了我們的創意、想象和關懷。經過了四五年的孕育期,等到歐萊雅品牌在中國確立之后,公益事業才慢慢地循序漸進地與商業推廣"分道揚鑣",直至大局已定、完全可以放開手去做。這也是我的一個理念:做公益事業之前必須要先把企業做好。
新民周刊:你在升任副總裁之前,曾擔任"對外交流及公共事業部"的總監。負責這樣一個開銷很大而無進賬的部門,會不會很有壓力?
蘭珍珍:1997年歐萊雅進入中國,不到一年后我就得到了現在這個職位,這是我自己提出的設想。在對最初的公關工作已經駕輕就熟后,我又對公關交流有了新的期望:我希望把這個行業拓展開來,不是單純地配合新產品的開發聯系媒體做宣傳,而是成為一個對公司的形象有影響,對公司的將來起一部分決定性作用的行業。當時我向公司提出了這個建議,但可能我想法也不是很成熟,并未得到上層領導的認可。他們覺得如果要實現我的計劃,整個公司的發展構思必須重新架構,沒有必要再興師動眾地作這樣的改動。但后來當我坦誠地與高層溝通后,老板說沒有問題,但是只有你一個人,先做起來吧。剛開始負擔真的很重,沒日沒夜地干。雖然沒有人來做績效考核,但我必須對得起公司、社會對我們的信任。這個期待是很沉重的,所以我反而比銷售人員更緊張,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公益≠捐款

新民周刊:參與公益中國評選活動的數百位候選人大部分都是企業界的成功人士,他們的簡介后面都附有一長串向疾病患者、慈善基金、希望小學等捐款的記錄。例如完美(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馬來西亞的華僑古潤金12年間在全國各地的各項捐款捐物已超過1億元,捐資建設了51所希望小學,而他的最終目標是100所。許路加當眾承諾:"我將拿出一半的利潤參加公益活動!"他曾向武漢市慈善總會捐助20000元,捐助身患白血癥的花季少女陳怡1.5萬余元、捐助因車禍致傷的8歲小男孩趙俊2萬元……歐萊雅在"10年公益之旅"中,為什么列出的卻是設立"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發起"保護長江、拯救白鰭豚"綠色行動;啟動全球美發師抗擊艾滋病教育活動等等?
蘭珍珍:這體現了民營企業家與跨國企業對于公益事業理解的不同。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大多為個案發起捐贈,沒有一個長期、連貫的理念,跨國企業一般不這么做。我覺得3000萬、5000萬,對偌大的一個中國真的只是滄海一粟。哪怕這些企業的財富再翻十倍,破產十次,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什么,不要認為把所有的錢拿出來就可以拯救這個世界了。
歐萊雅的做法是去倡導一種跟企業的價值觀相符合的理念,再以好的活動策劃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開一張支票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歐萊雅做活動的時候沒有采取這種簡單的做法,比較注重全社會的參與和互動,以及如何運作才能擴大這個公益活動的影響力,然后通過跟蹤了解互動的效果。
新民周刊:你如何在活動中實現這一點?
蘭珍珍:歷史上有許多的女科學家將畢生獻給了科學事業,然而直到20世紀上半葉,科學史上被提及的女性只有居里夫人。在中國我們聽到科學家們呼吁說:沒有博士生愿意跟著我們吃這碗苦飯。再不引起重視,科研就要青黃不接了。
1999年9月歐萊雅集團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簽署了"為投身于科學的女性"計劃后,作為國際計劃的延伸,在中國設立了"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這個獎項在中國設立3年以來,已經獎勵了14名杰出的青年女科學家,并發展成為針對中國對青年女科學家進行評選表彰的最重要的獎項之一。3年來,我們經常帶著女科學家們去高校作巡回講座,調查顯示,很多年輕人從只知道居里夫人,到第一年知道了考古學家侯亞梅、第二年知道了熊貓研究專家呂植、第三年知道了密碼學家王小云。最令人感動的是所有的女科學家獲獎后都把其中一半的獎金分給了自己的團隊,另一半用來總結科研成果。而呂植獲獎后,把她的10萬元獎金全部拿出來又開設了一個基金來支持那些年輕的科研人員。
再比如說我們西部的助學義賣。我們不是直接拿一筆錢給貧困學生做助學金,而是在校園中間中招募義工,采取了一個義賣的活動,由學生自己來運作。在這個活動中,義工和受捐助者都是我們所要影響的人。首先是通過我們的培訓,學生們在畢業之前了解了一個大型企業計劃從前期策劃到后期執行的全過程,讓他們真正體驗了什么是團隊精神、如何做一名職業人員。其次我們讓學生們經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親手把賺來的錢交給貧困學生,讓他們有條件繼續上學,有助于削減對于貧困學生的歧視和不理解。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學生都會受到感動,而他們感動之后發生的變化令人驚喜。家境貧困的楊再虹得到了我們的助學金后,她把這筆錢分給了比她還要貧窮,但沒有得到這個獎的學生。更有些從西部貧困地區來到校園的同學,再得到關懷之后毅然選擇畢業后去西部支教。
新民周刊:在公益中國的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一再希望歐萊雅能夠更慷慨一點,不知歐萊雅在公益事業上的投入是多少?
蘭珍珍:以校園義賣為例,4年來籌措了200萬善款,捐助了656位貧困大學生完成了學業。這個數字相對在座企業家的捐助金額實在是有差距,但是我完全不會低估我們項目的影響力。我參加過一次公益節目,當時主持人也問在座企業都捐贈了多少錢,國內的民營企業家們說的是2000萬、5000萬、8000萬,我說的是:"用金錢無法估計的價值。"所有的人看著我都有點吃驚。
新民周刊:你們會互相說服對方嗎?
蘭珍珍:當然他們很想說服我,但是我肯定不會被說服。我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就像你跟一個小孩講道理一樣,你肯定不會去在乎他最初所明白的道理,但是你也肯定知道,他以后長大了會明白更深奧的道理。我本人認為中國的民營企業對公益的理解還處于剛開始的階段,這已經比沒有好了,也非常感人。但如果我要談,可能會跟牛根生談得比較深入。他在民營企業家中比較前衛,正在運作一些基金會。我了解到他咨詢過許多先進企業的做法,請教了很多國際上的專家。
新民周刊:做公益事業還要去咨詢專家嗎?
蘭珍珍:你這個問題真好,我想強調的就是做公益還真的是要求教于國際上的專家,我自己就是如此。
新民周刊:看來公益事業除了愛心,還需要科學的運作機制,現在有咨詢公司認為一般企業和民間公益機構的投資績效偏低,應該交給專門的咨詢公司去運作。你贊同這種觀點嗎?
蘭珍珍:我認為可以在公司內部組織一個專門的隊伍來運作,給他們以專業的指導。但拿出一半的錢來付專家咨詢費,完全把公益事業外包給一家公司去做,我覺得這在目前的階段非常不現實。
公益之累
新民周刊:很多參與公益事業的企業家都遭遇過風險。獲得2006公益中國"最佳品牌公益行為獎"的北京振國腫瘤研究中心的王振國談到一名男子曾經在電話里向他勒索400萬元:"你不是很有錢嗎,捐給那么多人干嗎,別人還記不住你,給我我就記住你了!"許路加也說起他經常被騙,一周前還被別人以慈善名義忽悠走6萬元。你有沒有過這樣的危險經歷?
蘭珍珍:我收到過很多年輕人寫來的感謝信,從來沒有任何人向我要過資助。唯一的一次是在上海,有人在電視上看到我做的公益事業,就跑來坐著不走非讓我資助他。
新民周刊:為什么你遇到這樣的情形比較少?
蘭珍珍:我也在問這個問題,是不是經常被勒索也跟企業家自己的做事方式、表達方法有關。有些企業家經常被媒體報道他的慈善行為,又表現得很慷慨、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比較突出。而我代表的是一家國際性企業,如果我拍著胸脯說:這事兒我幫了,沒錢了盡管來找我!跟我的企業形象是不相稱的。反而會帶來負面效果,刺激仇富思想。
你必須要承認,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勒索富人的事情發生,露不露富不是關鍵,而是看你這個富是怎么樣一種方法去露。企業家如果精明一點,就不要去觸發嫉妒這種很奇妙的化學反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