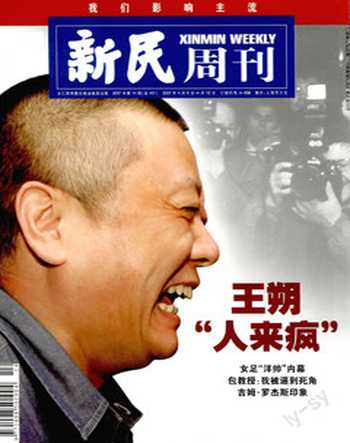一棵生機勃勃的“電影樹”
王宜文
《1945年以來的意大利電影》是江蘇教育出版社的大型專題叢書《電影館》的一本新譯著,這也是迄今內地出版的第二本意大利電影專著,1996年曾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了兩位內地學者編著的《意大利電影》,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竟然成為內地十年間唯一的意大利電影參考書,對于電影研究界和出版業來說實在是一件汗顏的事情。因而,《1945年以來的意大利電影》就顯得彌足珍貴,法國的電影學教授洛朗斯?斯基法諾簡要而全面地描述了二戰之后意大利電影的發展歷史與藝術特點,視野開闊、評析睿智。
意大利算得上是一個電影早熟的國家,當美國人還在廉價的"鎳幣影院"觀看粗陋的影像時,意大利已經制作出電影史上最早的場面宏大的豪華巨片。但浮華很快散盡,直到1945年之前,世界影壇幾乎再也找不到意大利電影的蹤跡;1945年的《羅馬:不設防的城市》標志著新現實主義運動的成熟,意大利電影再次走到世界前列,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世界范圍內現代電影興起的標志。《1945年以來的意大利電影》選擇這個關鍵年份為起點是要確立意大利現代電影的根基,其實早在半個多世紀前,法國著名學者安德烈?巴贊就已經指出了新現實主義的美學價值,其影響早已超越了意大利本土而成為世界電影寫實主義傳統的典范和源泉,也成為一個恒定的電影批評標準,比如,人們經常進行這樣的比附,伊朗導演阿巴斯的新現實主義特色,中國新生代導演賈樟柯與新現實主義的淵源等。
需要指出的是,《1945年以來的意大利電影》沒有簡單重復安德烈?巴贊的論斷,而是將新現實主義電影視為"一種整體的視角","告訴人們一個民族是如何成為一個規模宏大的故事的主角的",這就開辟了電影史研究的一個新維度,將電影與意大利民族意識聯系起來。作者認為,電影之前的19世紀是傳統歌劇維系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民族,20世紀后,電影繼承了歌劇的文化使命。新現實主義電影正是體現了這樣一個歷史契機,通過真實地再現意大利的社會生活,將二戰之后廢墟瓦礫中的意大利重新凝聚起來。在新現實主義時期,意大利電影實現了空前團結,既包括桑蒂斯、維斯康蒂等共產黨員,也有思想偏右的羅西里尼和德西卡這樣的電影藝人,他們呈現出相同的電影理念和藝術語言,雖然這個聯盟很快消散了,但是他們共同建立了意大利電影的根基,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所以,出現在該書結尾處的那棵"電影樹"有著特別的意義,透過這個維度可以窺見意大利民族現代文化的建構體系。
《1945年以后的意大利電影》指出,"1945-1948年間拍攝的影片中,新現實主義電影只占少數",當時的電影市場基本上被美國電影占據。這實際上是電影史上兩種電影文化的沖突,一種是主流的、娛樂的,雖然不排除文化建設的價值與意義,但主體上崇尚消費主義的即時滿足,如《天堂電影院》中人們的精神生活就呈現出一種虛假和逃避傾向;另一種電影強調思想與藝術,但往往曲高和寡,從未占據電影主流。傳統電影史的寫法通常以后者為核心展開,給人的印象的是電影似乎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這既不符合電影的"大眾藝術"特性,也模糊了電影史的真相。
《1945年以來的意大利電影》的作者也用很多篇幅描述意大利喜劇電影的發展,他認為喜劇性是發自意大利文化內里、自然天生的民族氣質。其風格源頭最早可追溯至16世紀以來的意大利即興喜劇,天才演員的即興發揮是其主要特點。這就使得新現實主義電影很快轉向所謂的"玫瑰色的新現實主義",以喜劇性調和新現實主義的苦澀與傷感。執導并主演《美麗人生》的羅伯特?貝尼尼無疑是意大利喜劇電影的最佳傳承代表。
《1945年以來的意大利電影》還用簡略篇幅分析了90年代意大利的電影狀況,作者將那些70年代之后的新導演歸為"后電影時期"人物,那棵"電影樹"已經無法界定他們的傳承關系,電視媒體和網絡媒體對娛樂市場的侵占,全球化浪潮下的制片環境構成他們的成長背景,他們和前輩導演一起面臨巨大的創作困境,以至于書中用了"預告的死亡"、"保衛意大利電影"等醒目的章節標題以顯示問題的嚴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