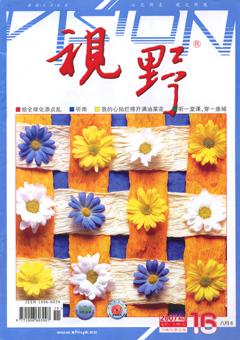給全球化添點亂
吳 強
每一次八國峰會期間,總會有眾多的示威者來給各國領(lǐng)導(dǎo)人“添亂”,所以八國峰會同時也是反全球化人士的“例會”。而G8峰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這次6月6日至8日的德國峰會這樣,出現(xiàn)如此涇渭分明的兩個政治舞臺:從今年3月起,德國政府斥資上千萬歐元,在濱海鄉(xiāng)村海里根達姆(Heiligendamm)興建了一條12公里長、2.5米高的鐵絲網(wǎng),將G8峰會首腦下榻的凱賓斯基飯店以及大約三百戶居民圈護起來,這條鐵絲網(wǎng)甚至伸入波羅的海3公里;而在這道隔離墻外,從5月中旬起,反對G8峰會的抗議者們也陸續(xù)駐扎在距離酒店數(shù)公里外的農(nóng)場空地上。
一道令人聯(lián)想起柏林墻的鐵絲網(wǎng),劃出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兩個世界。墻內(nèi),是代表全球化既得利益者的世界最富裕集團的工業(yè)八國;墻外,則是為窮國呼吁更多公平正義的來自全世界的近十萬抗議者。
抗議者:愿望有多迫切,表達就有多強烈
其實,從5月中旬起,就有成群結(jié)伙的抗議者們陸續(xù)來到海里根達姆附近的草地上,安營扎寨,與鐵絲網(wǎng)內(nèi)的白色度假酒店樓群遙相對望。來自德國、意大利、北歐和南北美洲各地的憤怒青年們做好了打持久戰(zhàn)的準(zhǔn)備,他們自行搭建帳篷,打造長桌長凳,甚至瞭望臺。他們在露天搭起大鍋,煮著蔬菜和通心粉,生活簡約而自然。德國電視一臺采訪時揶揄道,與他們相比,墻內(nèi)的G8首腦們,個個都是食肉者。
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代理人,默克爾政府對待示威者的做法與上世紀(jì)60年代相比,并未稍減暴力的運用,只是控制技術(shù)更為精準(zhǔn)。除了耗資1250萬歐元興建隔離墻,并以“零容忍”的態(tài)度來對付示威者,德國內(nèi)政部還調(diào)集了全國1.6萬名警察,組織了“9·11”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安全行動,并宣布峰會期間隔離墻外圍5到10公里的范圍內(nèi)禁止任何游行示威。不僅如此,從4月起,德國警方搜查了全國大約四十余處抗議組織者的辦公室和住所,從抗議者的電腦中尋找抗議示威的組織和人員資料,并收集他們的氣味標(biāo)本。如此種種,已經(jīng)被德國媒體充作嘲笑警方侵犯人權(quán)的搞笑素材。
但是,德國警方“零容忍”的政策并未能阻止示威的準(zhǔn)備。與僅僅3天的G8峰會不同,在海里根達姆會場外的反全球化示威早在峰會前一周就陸續(xù)進行,持續(xù)了10天之久。他們的表演當(dāng)然不在密室,而在街道。10萬名示威者的國籍也遠比八國更具全球性。
暴力抗議:抗議從來沒有什么純粹的形式
6月2日,在50個國家設(shè)有支部、擁有大約9萬名成員的阿塔克(Attac)會同其他組織,在鄰近的大城市羅斯托克組織了大約有8萬人參加的和平示威。如此聲勢浩大的游行在當(dāng)?shù)剡€是首次,即使在前東德時期也未見過。當(dāng)示威進入尾聲,警察的暴力鎮(zhèn)壓引發(fā)了“黑色軍團”的反擊,也演變成本次峰會反G8示威活動中最為慘烈的暴亂。沖突過后,近千人血灑羅斯托克街頭。其中,警察受傷433人,重傷30人,示威者受傷520人,20人重傷,另有128人被扣留。在八國首腦到達海里根達姆之前,燃燒的汽車、投擲石塊的黑色軍團、短兵相接的游行隊伍和鎮(zhèn)暴警察的畫面,就透過采訪峰會的媒體傳遍了世界。
參與示威的諸多反全球化組織在譴責(zé)警察暴力的同時,也譴責(zé)了黑色軍團的暴力示威。不過,無論從組織還是從行動上,暴力示威應(yīng)該歸為警察暴力的產(chǎn)物。6月2日當(dāng)天的游行,不僅為了反對本次G8峰會,更為了紀(jì)念40年前一名死于警察暴力的柏林學(xué)生。1967年6月2日,27歲的學(xué)生本諾·奧內(nèi)佐格(Benno Ohnesorg)在西柏林的游行中被警察槍殺,60年代的學(xué)生運動也從此進入一個轉(zhuǎn)折點——“6月2日”、“紅色旅”等極端左翼暴力組織隨后形成。類似的還有,2001年熱那亞G8峰會中,一名23歲的意大利青年卡洛斯·朱利安尼(Carlos Guiliani)在街頭抗議中被警察槍殺。這一意外死亡事件催生了黑色軍團,壯大了阿塔克。在本次峰會期間的鎮(zhèn)壓行動中,防暴警察事先摘掉了胸前的姓名牌和警號,以免被媒體錄像和被示威者識別。在爆發(fā)街頭沖突后,德國右翼的基社盟議員斯蒂芬·梅耶(Stephan Mayer)竟提議動用德國反恐特警來對付暴力示威者。而橡皮子彈的使用也被付諸討論,所幸德國警察工會的發(fā)言人在峰會前夕否認了使用不人道的橡皮子彈的必要。在1999年的西雅圖G8峰會期間,美國警方首次使用橡皮子彈對付示威者,造成嚴(yán)重傷害。
被德國警方視為本次峰會最大威脅的有暴力傾向的黑色軍團,屬于激進的“干預(yù)主義左派”,規(guī)模近8000人,參加本次峰會的成員在1000到2000之間。他們大多來自柏林的幾所大學(xué),頭戴面具,身著統(tǒng)一的帶帽黑色大學(xué)衫,防范被警方錄像事后甄別。他們回擊警察的辣椒水和警棍的武器是德國城市隨處可見的鋪道石——既是歐洲過去200年社運傳統(tǒng)的載體,也是常常令中國旅游者徜徉古舊歐洲街道、感受文明碎片腳感的來源。
對旁觀者來說,暴力的表達也許過于激烈,但與G8峰會一度壓倒一切的主題——恐怖主義,有著根本的分別,并未逾越人權(quán)的范疇。正如現(xiàn)任歐洲綠黨主席、曾為1968年學(xué)生運動領(lǐng)袖的科恩·本迪特所說,“抗議從來沒有什么純粹的形式”。對于黑色軍團或者所有參加反G8的示威者,他認為“抗議只是生命的感受,當(dāng)人們對社會不滿就需要表達”。這樣的表達,這樣的街頭行動,相比十幾公里外的密室政治,也許更接近問題的實質(zhì),更容易喚起世界對全球化危機的關(guān)注。
抗?fàn)幣c妥協(xié):全球化進程的修正
在寫于1944年的名著《大轉(zhuǎn)折》中,著名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家卡爾·博蘭尼作過一個經(jīng)典論斷: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社會的自救息息相關(guān)。在全球化時代,這一原則同樣通過反全球化運動對社會正義的訴求,開始扭轉(zhuǎn)全球化的方向,賦予其中更多的社會責(zé)任。與本次峰會同期開幕的科隆基督教教會日上,與會者發(fā)出了發(fā)展中國家、被忽視的人群“尊嚴(yán)需要公平”的呼聲。
在峰會期間,抗議者們舉行了一連串規(guī)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和露天搖滾音樂會;萬名示威者繼續(xù)沖擊會場外的隔離鐵絲網(wǎng);綠色和平組織的兩條快艇試圖闖進海岸禁區(qū)……但與此同時,大批國際非政府組織也云集羅斯托克,開會討論貧困、非洲、疾病、環(huán)境等具體問題。相比于樸素的反全球化姿態(tài),他們更具有“全球化另擇”的明確思路。
在這樣的氣氛下,默克爾的堅持終于獲得突破,6月7日的G8會談就大氣保護達成突破性妥協(xié),各方承諾在2050年前實現(xiàn)二氧化碳排放“減半”的目標(biāo)。6月8日上午,當(dāng)綠色和平組織兩支懸著“現(xiàn)在行動(Act Now)”標(biāo)語的熱氣球飄近峰會會場時,G8峰會的非洲論壇也邁開歷史性的一步:八國集團在未來5年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的抗艾滋病援助,并增加已有的發(fā)展援助,至2010年達到每年500億美元的水平。全球化的進程在海里根達姆完成了一次自我修正。
峰會結(jié)束后,德國媒體給予默克爾高度贊揚,稱其為“綠色總理”、峰會的“救世主”——默克爾政府挽救了峰會,回應(yīng)了反全球化運動的要求,也修正了全球化進程的方向。
(摘編自《南風(fēng)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