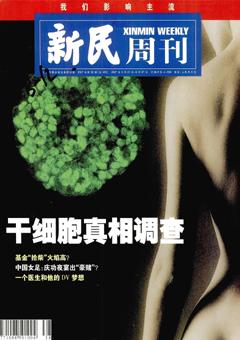成都雙年展:國畫REBOOT
王悅陽

“國畫也是當代藝術的一種,無論其有著如何深厚的文化底蘊,都不能放棄注入新的活力?它需要擁有更為開放的價值取向,才能積極投身于國際藝術之中,并在市場的考驗之下,找準自己的定位?”
2007年9月13日,一次以“RE-BOOT”(重新啟動)命名的藝術大展在成都拉開帷幕?這是“成都雙年展”繼2001年和2005年之后舉辦的第三屆藝術展會,也是日趨成熟的文化品牌一次全新的亮相?展覽的內容包括由61位藝術家參加的“主題展”?2位藝術家參加的“特展”,以及49位全國藝術院校的學生參加的“新人特展”三大部分?
REBOOT展以“水墨”為主題,對“中國畫”這一極為傳統的藝術進行新的闡釋,試圖從學術層面上重新定位中國當代水墨藝術,展現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與世界性之間的相互融合和置換關系?因此,該展既可視為一次向中國畫傳統的敬禮,更可視為一次中國畫未來的“導航”?
作為本次活動的藝術總監,重慶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馮斌參與了從策劃討論到接待安排的所有工作?馮斌對“國畫”有著不同一般的見地和實踐,在四川美術學院,他既是中國畫系的系主任,更是以力主“更新”?“創新”國畫而在全國獨樹一幟的“新國畫”代表性藝術家?在雙年展巨大寬敞的展廳中,馮斌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的專訪?
關注中國藝術的未來
新民周刊:“成都雙年展”是一個怎樣的展覽?它的緣起和特色是什么?
馮斌:成都雙年展從創立至今,舉辦了3屆?如果以1999年底成都現代藝術館建館后舉辦的“世紀之門:1979——1999中國藝術邀請展”算來,已經有8年了?無論是世紀之初藝術市場和藝術活動處于低迷之時,還是時下藝術市場日益活躍?社會各界對文化建設日趨重視之時,我們一以貫之地堅持著初衷:中國經濟的活躍和發展,必將作用于文化藝術?同樣,只有中國自己的文化發展壯大了,才會有中國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和諧共榮的景象?中國的崛起離不開文化的崛起?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支持和推動中國本土藝術的發展,促進和繁榮本土文化事業,就成為成都現代藝術館?成都雙年展一直堅持的理念?這也是為什么8年以來,我們不懈地以一己之力投入和宣傳藝術的緣由?
同時,從第一屆成都雙年展始,我們也把關注藝術的目光投向了新人?如果說,“主題展”呈現的是一種觀念意識上的“重新啟動”,那么“新人特展”更類似一場生機勃勃的行動的復蘇?49位藝術院校的學生懷揣最真實的藝術直覺和心靈沖動,義無反顧地在畫布上宣告了自己的再生?之所以是再生,是因為在藝術的荊棘地里,他們的生生死死,失敗困苦已難計其數?這一次的展出,是對他們才智和藝術的肯定?我們從千千萬萬新人中遴選他們?力推他們,正是由于他們美妙而神奇的藝術靈感,使得中國藝術生生不息,持續發展?關注新人,就是從發展的角度關注著中國藝術的未來?因此,“新人特展”也成為我們成都雙年展的最大的特色與亮點?
新民周刊:展覽為什么叫做“REBOOT”(重新啟動)?
馮斌:我們使用電腦時幾乎都有這樣的經驗:在使用電腦過久?或電腦的負荷過重而運轉不靈的時候,需要把電腦“REBOOT”(重新啟動)一下,或者“更新”系統,這樣才可以保證電腦的持續高效的工作?這就是我對這屆成都雙年展主題的理解,也是從電腦而到“國畫”的啟發:傳統藝術有必要“重新啟動”,也有必要常常“更新”,這既未損原來的系統,又能為其注入新的活力,并保證其持續高效地運轉?
新水墨?新國畫
新民周刊:當今國際藝術品市場的熱點是油畫藝術,國畫在很長一段時間已從市場的主體逐漸邊緣化?而且,以羅中立先生為代表的“四川畫派”也以油畫見長?展覽為何舍棄了具有較多地方優勢的油畫而選擇了以國畫為主題?
馮斌:我們習慣地說“國畫”,到底是指代特定的繪畫方式,還是指代特定的繪畫類型?或者還是如“國語”?“國文”一樣是指代“中國的繪畫”?雖然理論家們都加入到了這場歷經一百多年的論爭,其實就連名稱是“國畫”?“中國畫”或“水墨畫”,到現在也是眾說紛紜?所以,“國畫”對于我們來說,在今天依然是個需要面對的問題?
如果說“國畫”是指代特定的繪畫方式或者繪畫類型,那藝術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藝術沒有一成不變的方式和類型,而是不斷創新的?擴展的,“國畫”亦然?
如果說“國畫”是指代“中國的繪畫”,那何其繁多的方式和類型,該是哪一種可以擔當?又何以擔當“中國的繪畫”呢?
在去年底我們討論本屆雙年展主題時,“國畫”就成為了題中之義?我在草擬這屆雙年展的計劃時就明確說明:“‘國畫從一百多年前被提出,她作為傳統文化?本土文化的概念,在與‘西方文化的抗爭及自身的轉變中,其文化命題卻在政治的?經濟的種種干擾下沒有得以澄清,‘國畫在國際化的語境中如何進行當代轉換也問題依然——這顯然與中國社會經濟迅速崛起的進程不相稱?”
所以,在中國社會經濟迅速崛起,并得到國際上越來越多關注的大背景下,以“文化”的命題重新提出如此糾纏難解的“國畫”的問題,就是在于探討表征這一現狀的中國文化究竟應該是什么樣的?一個有悠久傳統文化的國度,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其文化又該何去何從?在經歷了藝術市場的潮起潮落后,在當代藝術的風風火火中,“國畫”是不暇他顧?或者是怨天尤人自期自艾?——此時此刻,關注“國畫”,更有全新的意義?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國畫”不是可以籠而統之的“中國繪畫”,也不是某種既定的方式和類型,而應該是可以從傳統資源中獲得轉換更新的?在今天世界多元文化中具有當代意義的?又有自己特色的開放性藝術?這屆雙年展正是希望把現有的各種“國畫”形態作一個客觀的概括,以此有相互之間的比較,并在比較中突現出問題的重點——在中國社會經濟迅速崛起的進程中,什么是其代表性的文化?
另外,我還要指出的是,新水墨究竟如何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與藝術創作實踐密切相關的問題?如果一個學者只是坐在書齋里,對已然出現的新水墨現象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肯定會出問題?對于這一點,人們只要認真研究本屆展覽參展藝術家們創作的許多優秀作品就會明白?他們在充分尊重水墨媒材特點的前提下,很好地開拓了水墨藝術的可能性?
國畫的定位
新民周刊:中國的傳統水墨畫藝術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歷了眾多發展與變化?從內容上,經歷了由“政治宣傳”向“表現生活”的變化;從形式上,從最初的徐悲鴻?蔣兆和等人的“素描加淡彩”,到以方增先為代表的“浙派”,直至今日,諸多藝術流派爭奇斗艷?反思這一發展過程,您認為當代水墨藝術的定位是什么?
馮斌:臺灣學者龍應臺女士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強調了“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的觀點?這與我們一向強調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觀點明顯不同?兩者的前提條件正好相反?我很贊同龍應臺女士的觀點?因為她的觀點乃是在新形勢下提出的,不僅對傳統觀點作了有益的補充,也對中國的水墨畫在當下全球化的格局中如何發展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反思自“文革”以來的中國畫藝術歷程,我認為有這樣四個變遷:
自80年代初起,由于脫離了“文革”思想的桎梏,思想解放運動蓬勃興起,藝術家對于現實社會?現實生活的關注與表現有了空前的提高,人文精神的復蘇給傳統國畫注入了全新的力量?我認為,當時國畫界的整體狀態,可以稱得上是積極投入社會變革,并緊跟時代步伐的?同時,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藝術家吳冠中先生提出了“要注重繪畫藝術的形式美”,倡導國畫藝術擺脫政治束縛,為國畫表現方式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到了1985年,國畫界發生了一件影響巨大的歷史事件:一篇《中國畫走向了窮途末路》的評論文章徹底否定了傳統,年輕的作者站在了傳統藝術的對立面,并在文章中影射?批評了一位當時極為著名的山水畫老藝術家?面對攻擊,那位老畫家并沒有正面回應,而是拋出了另一位比之更為傳統寫實的山水畫家,老畫家不僅大力推廣其人其藝,甚至還親自為之撰文,不遺余力地進行宣傳?他的目的很明確,希望當時的年輕人能看到傳統藝術的優秀一面,認識傳統藝術的博大精深?一石激起千層浪,關于傳統還是創新的爭論展開了,圍繞傳統藝術的取舍問題,國畫界開始陷入了喋喋不休的爭論怪圈,國畫也由此開始逐漸脫離了社會?
直到80年代末,當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大,西方當代藝術不斷沖擊著中國藝術家的視野,眾多年輕的油畫家開始了新的藝術探索與個性解放?但此時的國畫界出現了什么?出現了“小腳女人”?“紅肚兜”!一大批所謂的“新文人畫”應運而生?這群過著現代生活的國畫家們不斷地重復著古人的腳步,這完全就是逆時代而為!我們的水墨畫談何發展?
好在90年代以來國內經濟迅速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藝術市場的發展?國畫也因此成為了社會商業品,享受到了藝術品市場的“第一桶金”?根據市場的不同需要,國畫也逐漸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但到了本世紀初,由于市場的魚目混珠,以及中國當代藝術的蓬勃興起,國畫逐漸退出了市場主流,油畫取代了它的位置?作為我國獨有的藝術,國畫在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中,不僅沒有很好地表現?反映日新月異的生活,甚至完全游離于社會進程之外,令人擔憂?
或許,我們的展覽并不能對于當代水墨畫藝術的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大家認識到:國畫也是當代藝術的一種,無論其有著如何深厚的文化底蘊,都不能放棄注入新的活力?它需要擁有更為開放的價值取向,才能積極投身于國際藝術之中,并在市場的考驗之下,找準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