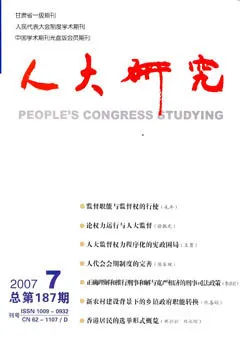正確理解和推行刑事和解與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動著刑事法律政策的調整。寬嚴相濟是我們一貫的刑事政策,長期以來得到較好的貫徹執行,有利于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刑法任務的實現。在新的形勢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充實了新的內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了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意見、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等規范性文件。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向大會作的報告,這兩個報告也充分闡明了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具體要求,各類媒體對此如實客觀地作了報導。在貫徹寬嚴有機統一,該嚴則嚴,該寬則寬,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強調對嚴重犯罪依法從嚴懲處,對輕微犯罪依法從寬處理,對嚴重犯罪中的從寬情節和輕微犯罪中的從嚴情節也要依法分別予以寬嚴體現,對犯罪的實體處理和適用訴訟程序都要體現寬嚴相濟的政策中,積極探索著一些有效的途徑,如刑事和解。從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刑事和解調解審結的案件大體分為兩類:一是刑事自訴案件,二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刑事自訴案件一般是輕微刑事案件,可以進行調解,這在刑法、刑事訴訟法中規定較為具體,爭議不會太大。然而,對于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案發后真誠悔罪并積極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案件,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有人把它看成是“賠錢減刑”、“以錢買命”、“以錢買刑”,認為這樣做違背了司法正義。這種宣傳是對刑事政策的誤導,把“可以”當成了“必須”,把“一個”情節等同“全部”情節,把“慎用”等同“不用”,因而消弭了該政策本身的積極方面,放大了該政策在執行中可能變異的偏頗性。
刑法、刑事訴訟法及刑事政策是一門科學,有其客觀規律性可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作為先進文化的代表者,我們在這一方面吸納了古今中外可供借鑒的某些成果;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為我所用的東西也作了很大改革推進。媒體上介紹、研究的清朝議罪銀、國外辯訴交易、非合意性、合意性等概念,與我們現行的刑事制度和政策是不能等同的,也不好類比。比如說我國的公、檢、法、司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體制,以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就具有符合我國國情、促進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尋求社會公平正義法治建設的鮮明特征。
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兩院”報告的相應提法和一些地方不斷探索的這方面做法,其積極意義在于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依據法律框架原則制定的刑事政策,指導刑法、刑事訴訟法的實施時,有重點,有側重,但這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作調節。也就是說,在實踐中從寬、從輕、減輕不能突破法律已明文規定的界限,自然也不能概之為“以錢買命”,要防止過寬或過嚴的兩種傾向,特別要注意糾正一味從重從快的慣性思維:首先要把過失與故意犯罪加以區分;其次對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其對社會的危害性,要作清醒的、充分的評價,在故意犯罪中要注意把主犯、累犯與偶犯、初犯、從犯加以區別;再次要注重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一方面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要用好刑事法律政策予以保護,另一方面對未成年人犯罪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已賠償被害人損失并取得被害方諒解,雖然是在犯罪后,但也能說明其社會危害性已減輕的,在法定范圍內從輕、減輕或不起訴或從寬處理,都是指刑法已有明文規定的情形。當前,對于親友、鄰里及同學、同事之間糾紛引發的輕微刑事案件,已認罪悔過、賠禮道歉、積極賠償損失并得到被害人諒解,或者雙方達成和解并切實履行之、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給予從輕、從寬或不予刑事處罰,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
同時,為了更好地保護被害人及其親屬的合法權益。我們要探索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辦法。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一些代表提出議案,提出建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我國的司法實踐在這方面也有較大進步。被告積極對被害人賠償的似也可以作為救助制度的組成部分或補充。當然,對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制度還可以從更高更廣的層面來調動各方積極性,使之做得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