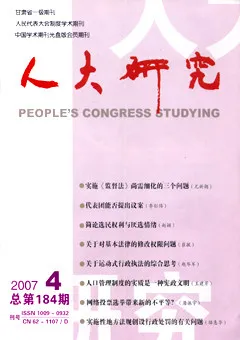關于運動式行政執法的綜合思考
為加大整治“黑車”的力度,2006年4月24日起,某市下轄的16個委、辦、局掀起為期一個月的“狂飆行動”。按照該市發布的《依法查處取締無照營運行為的通告》,期間查獲的黑車一律處以“極刑”,即不論車型全部按照上限50萬元的標準予以罰款,如果第二次被查,除被罰款外,車輛將一并沒收。但據《瞭望新聞周刊》的報道,該行動中雖有不少“黑車”落網,但更多的是暫時休整或 “戰略轉移”到打擊力度相對薄弱的遠郊區縣,而那些地區原本就是“黑車”在城郊結合部的聚集地。整治“黑車”的效果并不理想,黑車問題在治理行動結束后依然嚴重[1]。
此類“狂飆行動”即為本文將研討的“運動式執法”。這種執法形式,在當前屢見不鮮,其效果究竟如何,又有何利弊?在切實推進依法行政的進程中,我們應該怎樣更好地加大治理力度,整治違法違規現象?
一、運動式執法的現狀
在日常生活中,“集中整治”、“專項治理”、“××行動”、“××戰役”等詞匯常見諸報端。通常,很多執法部門也習慣于集中優勢人力物力,在限定的時期內對違法現象形成“拳頭”攻勢,以取得突破性成果。這種執法方式,老百姓稱之為“運動式執法”。
運動式執法通常具備以下三個特征:一是由于某一社會問題的嚴峻形勢為群眾和政府所關注,出現集中整治的必要性;二是政府有關部門在短期內按照部署,最大限度地動用自身資源,形成合力對某一凸現的社會問題進行集中清理整頓;三是執法行動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展開,以執法的高壓取得短期成效,突擊過后往往疏于治理致使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反彈。
某市的“狂飆行動”,為我們提供了考察運動式執法的一個范例。根據該市運輸管理部門統計,在開展行動前,該市“黑車”數量已達6~7萬輛,而本市正規出租車的數量僅在6.6萬輛左右。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5月底,該市共依法查扣各類“黑車”12921輛,依法對從事非法營運的9940人作出行政罰款等處罰。其間,公安機關對非法營運人員中敲詐、傷害乘客及出租汽車司機、為爭搶生意滋事以及阻礙抗拒執法的行為,依法刑事拘留33人,治安拘留340人。
“黑車”整治行動的效果如何呢?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常坐黑車的居民反映,“黑車”并沒有減少,只是向執法力量相對薄弱的地區進行了轉移,在城郊的醫院、小區門口、車站周圍,“黑車”還是很活躍。某市交通管理局有關人士也坦承,“狂飆行動” 雖然使各類非法營運行為較整治工作開展前明顯減少,但城郊接合處的“黑車”整治情況仍不理想,城區的反彈現象也很嚴重,“打擊‘黑車’非法運營,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事實上,類似“狂飆行動”的運動式執法,很多部門一直以來就在廣泛使用。例如,在刑事執法活動中,一般以打黑除惡、掃黃打非的嚴打行動最為典型;而行政執法活動中,則常以專項治理、集中整治等等形式出現——2000年3月29日,河南省焦作市錄像廳大火后,全市742家錄像廳、歌舞廳、游戲廳被關閉;2002年1月,江西省由于發生特大煙花鞭炮爆炸,要求全省從花炮產業中退出;2004年,安徽省阜陽市劣質奶粉毒害嬰幼兒事件被披露后,全國各地掀起了圍剿害人奶粉的“高潮”,30多個牌子的劣質奶粉被列入“黑名單”,奶粉市場一時蕭條沉寂;2005年出現的“蘇丹紅”事件,使人們談“紅”色變,執法部門為此掀起了圍剿“蘇丹紅”的執法風暴;2006年由于狂犬病疫情和“狗患”引起的矛盾,云南牟定、山東濟寧以及南京、北京、深圳、武漢等市重拳出擊,掀起治理狗患的打狗風暴……
二、運動式執法的原因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多的運動式行政執法行為呢?應當說,在我國當前的社會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