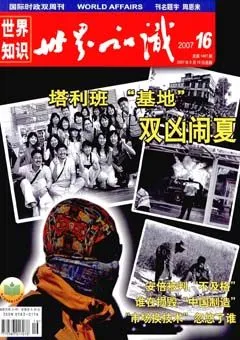從屈辱感到斯德哥爾摩情結
百年帆影
李揚帆
北京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博士

晚清以來中國大國地位的喪失導致一種普遍的民族屈辱感。屈辱感既然是時代變遷的必然后果,我們就不得不學會長期與之共處,并學會從中走出。于是,民族復興成為目標。但我們驚醒過來、走向復興的時候,突然發現一個難以逾越的情境:他們(西方)把一切國際事務的規則都安排好了,我們只能接受。從恢復聯合國席位到加入WTO均暗示了中國接受西方規則的事實。這種接受是由不情愿到情愿的一個轉化過程,我們用“全球化”這一模棱兩可的詞語為我們行為找到了正當性。恰恰是這種正當性證明了我們接受國際規則的一種斯德哥爾摩情結,即:在本質上,我們還是認為當代國際關系的規則是不平等的,是充滿西方霸權罪惡的,但是,為了生存,我們從不得不接受并進而轉化為這種規則找到正當的借口。
在確立新的民族發展目標上面,中國長期受一種屈辱感壓抑,對于地位和尊嚴等問題存在高度的剛性和敏感性。此外,它還帶有一種嚴重的復仇心理,明確的目標是日本,不明確的目標是“外部世界”這個含混的概念。
如何改變“被羞辱”的狀態,甚至實現“復仇”的抱負呢?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或者說“崛起”,或者說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崛起的提法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這個詞匯是個“舶來品”。但是,中國崛起的夢想或者說大國夢想從洋務運動時期就已經存在,并經過新中國的發展成為國家目標。后冷戰時代的中國崛起提法,具有更加具體的國家戰略的意味。
從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背景來看,約瑟夫·奈認為,“實際上,‘中國的崛起’是一個誤稱。‘復興’要準確得多,因為這個中央王國在歷史上以及按照國土面積衡量,一直是東亞的大國”。中國人自己認為崛起是理所當然的,而國際社會對中國這個目標、夢想或者戰略的看法,可能完全和中國人自己的想像不同,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在中國崛起這個問題上,存在相互溝通的困難和障礙。國際社會可能把它當成是對當今世界的沖擊,并對中國的愛國主義充滿疑慮。而國際社會的疑慮又反過來導致中國人對外部世界充滿敵對情緒,并對外部環境做出過于嚴峻的估計。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發展的困境。中國要成為大國的主張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的意識。但是,中國社會從總體上而言,并沒有脫離農業文明的發展階段。這種歷史階段具有特定的思想影響,它導致中國人短時間內無法具備世界性的眼光,認為只要每個國家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沒有必要去關注或者“管”世界他國的事情。
當然,正是因為我們曾經被羞辱,所以我們對和平、平等、和諧和非戰等等價值抱有誠實的夢想。
事情的尷尬處在于,如果我們過于把上述價值當成我們堅決的主張,就必然和西方的霸權和西方的優勢發生沖突,而我們又不得不在這種霸權體制中謀求生存。
當生存成為第一法則的時候,價值觀就會退讓給這個首要目標。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由此產生。
所謂斯德哥爾摩綜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