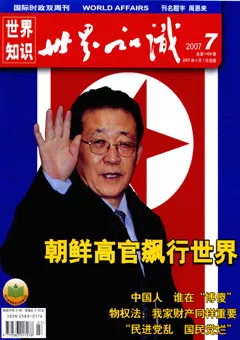巴金,令人深思的誤讀
李兆忠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1934年秋,巴金出于“到日本看看的興趣”,化名東渡日本。經朋友事先介紹,他住進橫濱商業學校一個姓武田的漢語教師的家里。三個月后,因無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經拜佛而搬出。巴金的小說《神》就是根據他這段生活經歷寫成。
小說描寫一個叫長谷川的日本小公務員,由一名“無神論”者變成一個“有神論”者以后對神的狂信,以及“我”對這種行為的全知全能的分析批判。其中有一個細節:主人公的藏書里,除了大量俄法進步作家的文學名著,還有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巴枯寧和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大杉榮、河上肇等人的著作。40年后,巴金在回憶錄里仍清楚地寫著:“我住在武田君的書房里,書房的陳設正如我在小說中描寫的那樣,玻璃書櫥里的書全是武田君的藏書,這些書可以說明一個事實:他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信神的人。”
東京大學文學部一位教授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神》的主人公長谷川與其原型武田之間存在著原則性的差異。現實生活中的武田,并不是一個曾經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個屬于右翼的漢語教師。當初出于“雄飛大陸”報效大日本帝國的志向選擇了漢語專業。侵華戰爭爆發后,他自動辭去商業學校副教授職務,作為日本軍隊的少佐翻譯來到中國,參加侵占濟南的戰斗。此后,他先后在張家口、包頭等地的日軍特務機關任職,為日軍侵略中國盡犬馬之勞。這位教授就此疑惑寫信請教巴金,謎底才解開。巴金回信說,那些有思想問題的書,并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學書,而像蒲魯東、巴枯寧、拉薩爾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蕆書。他還辯解說,《神》是小說,不是新聞報道,人物與故事沒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實。
巴金的辯解不無道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對武田這個人存在著嚴重的誤讀。現實生活中的武田,絕不是巴金想像的那樣,假如能作歷史還原的話,他只能是一個思想保守、愚忠天皇,并且有著日本人獨特的“曖昧”性格的男子。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巴金的誤讀?
巴金具有超常的人格氣質,他豐沛的道德激情與精神焦慮必須隨時通過寫作得到釋放,更何況,此時巴金已在西方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理論里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對立的歷史進步觀的熏陶,是一個早熟的“世界公民”,一個激進的人道主義者。這兩種因素的互相激蕩,決定了巴金的敏感與注意力總是集中在與人類的苦難相關的現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愛、正義這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上,而對民族性、國民性、地域文化之類視而不見。這種心理預設與知識背景,決定了巴金看日本的眼光。
巴金認定武田過去是一個“無神論者”,惟一的證據,就是聽說武田過去不念經信佛。這個并不可靠的證據,在眼前所見的刺激下,啟動了巴金頭腦里早已預設好的人神二元對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信神的人”,于是虛構了主人公有大量進步藏書的細節。這個虛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記憶中終于變成了真實。
以西方“有神”與“無神”二元對立的觀念解釋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來就牽強。日本是一個“人”“神”難分的國度,求神問佛,在日本是家常便飯;如果一定要作區分,那么只能說,絕大多數日本人都是“有神論”者,但這個“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泛神意義上的祖先神、自然神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萬世一系”的“活神仙”——天皇。巴金在日本游歷的時候,正是這個“神”大發其威、神力登峰造極的時候,包括武田在內的許多日本文化人成為侵略中國的鷹犬,都是這個“神”激勵的結果。可惜如此重要的現實不在巴金的視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島國根性”,就這樣輕易地被消融到了“人類”的普遍性中。
武田熱衷于念經求佛,其實并非無跡可求,小說里有一個細節:長谷川恐懼地對“我”表示,今年正好是自己33歲的“兇歲”。這個被巴金一筆帶過的細節,也許是武田成為“有神論者”的真正原因。按照日本的習俗,處在“大厄之年”的人,要舉行各種消災禳解的儀式,比平常更多地敬神拜佛,過了這個時期,則一切恢復如常。生活中的武田,正如巴金后來回憶的那樣,并沒有像小說斷定的那樣“跳進深淵”,而是恢復了常態。假如巴金對日本的宗教生活與風俗習慣有足夠的了解,或者退一步說,假如他不是那么自信,不屈從急近的寫作沖動,能以冷靜之眼審視日本的生活,情形也許是另一種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