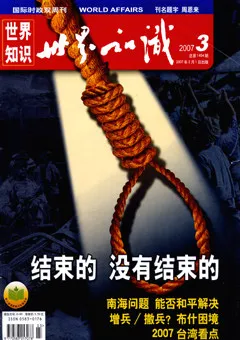醫保制度:環球同此涼熱

丁 純
復旦大學歐洲中心常務
副主任
歲末年初,國內媒體公布了過去一年中百姓最為關注的社會問題排名,醫保取代往年的就業、反腐問題躍居首位。聯想起中央政治局專門的醫保學習會以及胡錦濤主席的重要講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下醫保已成為中國百姓和領導最為心憂的話題。
無獨有偶,在醫保制度的發源地德國,履新的默克爾政府一攬子改革舉措中首個亮相的也是醫保制度的改革,引起朝野紛爭,醫生上街游行,患者抱怨不斷,成為繼世界杯后令生性沉穩的德國人沸騰的新熱點。
醫保制度之所以如此吸引公眾的眼球,無非一是因其重要性,二是由于目前各國醫療保障制度不完善。健康之于眾生,正如德國著名哲學家叔本華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健康并非生活全部,如無健康則一切皆為虛無。”關于各國醫療保障制度,盡管在決定人的健康的因素中,醫療只占8%,遠在個人行為和生活方式(60%)、遺傳(15%)和社會、經濟因素(10%)等之后,但作為維持健康和搶救生命的最為直接的手段卻最受重視。因而,以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為核心的包括醫療服務、醫療保險、醫藥等“三醫”在內的醫療保障制度模式及其績效,自然也就成為各國民眾或詬病或贊許的熱議對象。
當今全球的醫療保障制度普遍突出的問題,集中在財政的可持續性和制度的公平性(衛生服務的可及性)上。前者來源于醫療費用的持續攀升,造成入不敷出。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數據顯示:全球醫療費用占GDP的比重從1948年的3%增至近年的近10%。究其原因:有日益加劇的老年化的困擾,醫療、醫藥技術進步的助推,以第三方付費為償付特征的醫保制度的缺陷,以及人們健康觀念的嬗變和對“人人享有衛生保健”承諾的認識深化。而公平性的問題,主要反映在醫保程度和醫保制度的覆蓋面上。
從具體國家來看,各國實行的醫保制度差異頗大。追根溯源,從1883年德國在俾斯麥領導下頒布《疾病保險法》,建立起世界上首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以來,先后分別形成了以德國、英國、美國和新加坡為典型代表的四大醫療保障制度模式:社會醫療、全民醫療、商業醫療和強制儲蓄式醫療保障模式。四大模式各具特點,其中德國模式覆蓋面寬,主要由雇主、雇員各自分攤、繳納醫保費用來籌資,社會自治醫保機構地位突出;英國模式覆蓋全民,籌資則通過一般稅征集,政府對醫保的參與度高、控制力強;美國模式除服務65歲以上老年人群的醫療照顧計劃和覆蓋貧困人口的醫療資助計劃外,主干是面對中產階層的商業醫保,覆蓋面相對較低;新加坡模式則突出強制儲蓄籌資方式。
綜觀四類醫保模式的績效表現,著名經濟學家費爾德斯坦的結論恰如其分:“現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醫療保險制度是完美的和可以作為榜樣仿效的。”德國模式的缺陷是費用上漲過快;英國的弱勢則凸現在廣覆蓋、高公平性遭遇有限的政府預算約束,由此引起醫療服務效率低、看病候診時間長;美國模式弊端則不僅費用高昂,2003年人均逾5711平價美元,且公平性差,至今尚有14%的國民沒有醫保;新加坡模式的短處則是互濟性弱、且資金價值受金融市場影響大。
有鑒于此,各國先后展開了具有針對性的改革。費用上漲過快的德國祭出了提高患者自我承擔的部分,在醫院、醫生間引入競爭機制的抑價利器。公平性高、但效率低的英國通過引進“內部市場競爭”的方式,加強競爭、提高服務效率。公平性差、費用高的美國多屆政府都試圖將覆蓋面擴大到全民,克林頓總統在任內專門組成了以希拉里為首的醫改委員會,通過推行“管理式保健”,微觀上遏制費用飛漲。新加坡通過增加政府投入的做法增強籌資的公平性。一句話,都在提高效率和公平上下功夫。
筆者以為:各類模式的趨同正好為我們的醫改提供了思路:抓住醫療服務領域改革這個核心,加大政府對公共衛生和初級醫療的投入,同時逐步將覆蓋面擴大到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公民,加大公平性。
欄目主持 沈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