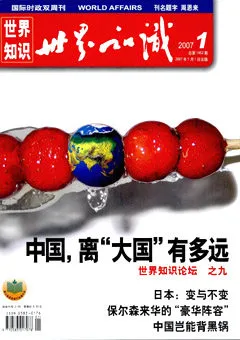國中之“國”
國中有國,成因各異,可簡括三。
一是純自然地理意義下主權平等的“國中之國”。
在廣袤的南非版圖上,沿著馬洛蒂山脈和德拉肯斯堡山的南非中心地帶,鑲嵌著微型的山地小國萊索托。19世紀初,一場席卷南部非洲的“部落戰爭”開始加速南部非洲從“部族”走上“國家”之路。南部索托族人在首領莫舒舒一世的率領下進入山區,開辟家園,建立王國,國名為萊索托。由于萊索托地處秀美的非洲高原,又是南部非洲為數不多的君主制國家,世人皆稱它為“天空中的王國”。
萊索托是南非的“國中之國”,它被南非環抱,但憑借天然的地理屏障,依靠東部山地和高原,門戶主要集中在西部一條40公里寬的狹長低地,形成了易守難攻的理想棲身家園,不僅南非前殖民統治者布爾人的洋槍洋炮沒能攻占當年生產落后的萊索托,它竟也沒被龐大的南非所吞并。它與南非是各自主權平等的兩個國家。
萊索托有豐富的水利資源,但沒有相應的發電能力,而南非則缺水嚴重,擁有超一流的發電技術。于是,水電工程把萊索托和南非緊密聯在一起。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各種國際組織就一直在為“萊(萊索托)水南(南非)調”、“南(南非)電送萊(萊索托)”項目籌集資金,以圖解決非洲嚴重的人畜飲用水和農作物種植灌溉水的缺少問題及電力短缺問題。90年代初項目正式啟動,所需資金主要由世界銀行承擔。一期工程預算投入26億美元,但事實上已超出了11億,二期工程也超出了預算,而且工程質量沒有達到預計水平,至今都還沒有進入可運行狀態,頗讓人遺憾。
第二種“國中之國”則起因于政治文化事件,通過特殊的政治安排而形成特殊的“國中之國”現象。
2006年11月27日,加拿大眾議院通過了聯邦少數黨政府總理哈珀提出的動議,正式承認魁北克為統一的加拿大的“國家”,形成了世間罕見的“國中之國”現象。
魁北克位于加拿大東部,是加拿大面積最大的省,絕大多數人為法國人后裔。長期以來,魁北克分離主義者主張魁北克政治上實現獨立,經濟上與加拿大其他地方保持聯系,即“主權一聯系”的主張。這一主張成為各屆政府面對的難題。哈珀上臺后,面對分離主義者的壓力,在這一問題的關鍵性的角色定位上用模棱兩可的語句,對“魁北克人”和“國家”作了狹義性解釋,使“魁北克人”只指向以法語為母語并占70%人口的魁北克人(Quebecois),而非普指的魁北克人(Quebecer),“國家”則非國際法實體意義上的主權國家(Country),而是以文化和語言所構筑出來的“民族體”(Nation)。哈珀獲得了炫目的成功,包括魁入黨在內的其他三個黨團都支持了哈珀的動議,在308個眾議院議席中共斬獲了266張支持票。
不過,這種只停留于文字游戲中的掛一漏萬的“反分裂法”,雖然沒有給漸進獨立的魁北克分離主義者真正劃出實質意義上的法理底線,卻扔出了一艘可以搭乘的獨立之舟,它將誘惑各類分離主義者們再次將形同魁北克一樣問題的各“民族體”駛入大西洋的獨立之海。以因紐特人和阿留申人為主體的原住民社區已經表示,既然魁北克成為哈珀主義下的“國家”,他們更有理由成為哈珀式的“國家”。
第三種“國中之國”現象則出現于一國的主權領土失去有效政府規范從而事實上形成了一個平行“國家”的情況中。這個可以舉巴基斯坦境內與阿富汗交界處“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殘余分子占山為王的例子。
2006年初,不斷有媒體報道,“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殘余分子宣布,他們已經控制了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處的北瓦濟里斯坦的大部分地區和南瓦濟里斯坦的一部分地區,并已經在這塊土地上成立了一個“瓦濟里斯坦伊斯蘭國”,儼然把這塊土地視為已有的“國中之國”。
不過,即使這樣的國家事實存在,它也是非法性的。正如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發出的警告一樣,如果你們膽敢出來活動,“真主會打斷你們的脊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