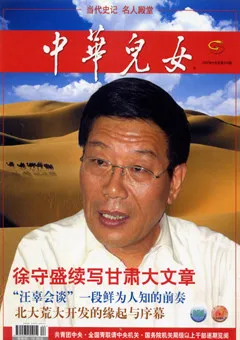“汪辜會談”一段鮮為人知的前奏
大凡交響樂團上臺后,在宏大的樂曲正式演奏之前,演奏員們都先要與首席小提琴手進行對音。1990年4月,從臺灣地區(qū)轉道香港經廈門、杭州來上海的一位神秘客人通過華東師范大學的馮契教授與已卸任多年的老市長汪道涵先生進行了一次鮮為人知的政治“對音”。三年之后的1993年4月27日,兩岸代表終于在新加坡舉行了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今天,三位直接進行對話的人中有兩位已經作古。我作為17年前那次對話的牽線者,現(xiàn)將自己所了解和經歷的情況作一個大概的回憶,以饗讀者。
一位神秘客人的來訪
1990年4月,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接待了一位來自臺灣地區(qū)的客人——臺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的弟子張尚德教授。張尚德先生于3年前受南懷瑾先生要其訪問大陸地區(qū)的囑托,經數年的準備終于成行。張尚德先生畢業(yè)于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曾任中國(臺北地區(qū))哲學學會總干事、文化大學教授及十方禪林書院博士班主任,是臺灣地區(qū)著名的禪門宗師,此行有意在內地委托一家印刷廠印制禪學研究書籍在祖國大陸進行交流。還聽說張先生帶有巨額投資意向,欲尋覓與上海市主要領導會面的機會。
當時任華東師范大學校長的袁運開教授和學校外事辦公室根據對方欲與上海市領導層會面的要求,在張尚德先生一行來滬之前就通過各種渠道與上級有關部門多方聯(lián)系,終無結果。在這樣一種國內外風云際會復雜而又敏感的政治背景下,市領導似乎無意會見這位說不清道不明的臺灣民間人士。
此時,負責與張尚德進行學術交流的馮契教授把我找去,問我:“聽說你有辦法與汪道涵取得聯(lián)系?”我回答說:“我有一位親戚在國務院外經貿委曾與汪老同過事。去年《社會科學》雜志(我所工作的單位)成立十周年時我曾經請他為雜志題了詞。”馮先生對我說了一些張尚德先生來上海的意圖,基本證實了李志林先生所講的那些話,馮先生希望我能聯(lián)系汪老,請他出山與臺灣客人見一面。我嘴上答應了下來,但一提起“臺灣”二字,卻心有余悸。
聯(lián)系請汪道涵出面的事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的姑父高業(yè)茂,上世紀40年代在河南大學任歷史系教授,系國民黨政府的立法委員。1949年赴臺灣。盡管出身于中國早期工業(yè)家家庭又有這樣一位舊官僚姐夫的父親在解放初期就加入了共產黨,但我在1968年赴黑龍江建設兵團下鄉(xiāng)時仍因這樣一位臺灣的“海外關系”而被打入另類,不能當“兵團戰(zhàn)士”,被壓在了政治最底層。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我參加恢復高考后的首屆招生考試,才終于圓了自己的大學夢。這些經歷和方方面面的政治陰影始終在我心頭揮之不去。但面對我所尊敬的師長、學識淵博而又心地坦蕩的馮先生所托,我又稍稍有所慰藉,畢竟,“文革”已經結束十幾年了。
我開始試著與市府顧問汪辦聯(lián)系,接電話的方秘書回答:汪老沒空!第二天又打電話去,得到的回答依舊是這簡單的四個字。我如實向馮先生匯報。馮先生也一籌莫展,他只好說再聯(lián)系聯(lián)系看。情急之下,我冒昧地直接往汪老家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汪夫人孫維聰女士,我怕再次被擋駕,先將我與汪夫人在黑龍江大學工作時所尊崇的杜老先生的關系抬了出來(據說當年孫女士在與汪老結為秦晉之好前,還專門征求過杜老先生的意見,可見他們之間的熟識程度),在得到汪夫人的認可后,又說明了我與汪老的老同事、當時任外經貿部顧問的石部長之關系和來意,終于,汪老接起了電話。我在電話中先說:南懷瑾先生您認識嗎?他說:我知道。我遂將自己所了解的張尚德先生此次來滬的情況和用意依葫蘆畫瓢般一一道出,并轉達了張先生和馮先生邀請他參加26日華僑飯店午宴的事。特別提到張先生帶了50億美金投資意向的事,當時,在我有限的感覺中,認為這似乎是重中之重的事了。汪老在電話中未表示任何態(tài)度。
儒宦、哲人和禪師開始了兩岸歷史上的一場特殊對話
4月26日上午9時。張尚德教授在地處上海市中心附近的華僑飯店9樓松鶴廳作了整整一天的“禪的超越性”報告。下午4點半,在報告會接近尾聲時,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丁禎彥教授突然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告知我:快!汪市長(當時人們出于尊敬,對已卸任的汪老仍這樣稱呼)馬上就到,你趕快跟馮先生下樓去接客人(事后得知,華東師范大學校長辦公室在那一刻剛接到汪辦打來的電話,通知了汪道涵先生要來華僑飯店會見張尚德先生的消息。辦公室工作人員馬上驅車趕到飯店通知了馮先生)。我急忙陪馮先生、張先生一起下樓去接汪老。到了樓下,不一會兒,只見汪老輕車簡從,僅帶了方秘書一人從一輛黑色的奧迪車上走出,正走上大門前的臺階,華僑飯店飲食部趙雅美副經理即刻已安排工作人員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大宴會廳隔出一間小會客廳,并將汪道涵先生、馮契教授、張尚德教授引入會客廳……
此刻,一位儒宦(當年解放日報評論員“皇甫平”成員、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同志在回憶錄中對汪老的尊稱)、一位哲人和一位禪師開始了兩岸歷史性的對話。出乎我意料的是,三位先生的對話主旨從佛學、禪宗、投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天地、祖宗——孫中山、博愛、天下為公——制度、主義、信仰——和解、家和、國興——漸漸地進入了兩岸關系……按照國內媒體慣常使用的話來說,會談是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汪老談興盎然,原打算一個小時的會見又延續(xù)了半個小時。最后,汪老風趣地笑吟了一首客家民謠贈張尚德先生的秘書(吳秘書祖籍系廣東梅縣客家人):“臨別贈送酒一杯,望君早日衣錦歸;路邊花兒切莫采,家中還有一枝梅。”會見完畢,已將近6時,我跟著馮先生、張先生又將汪老送至樓下上了車。
后來事情發(fā)展的臺前幕后
這次上海會面之后,兩岸加快了民間交往的步伐,1990年11月辜振甫先生出任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同年12月31日始,兩岸密使在南懷瑾先生香港的寓所中重開國共兩黨會談。1991年12月汪道涵先生出任海峽兩岸關系協(xié)會會長,并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協(xié)會”和“海基會”在香港以民間機構的形式舉行了會談,達成了“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識”,“共識”成為以后兩岸正式對話與談判的基礎。
從南懷瑾先生的囑托到張尚德先生的成行,前后準備了三年,從1990年4月26日跨越至1993年4月27日“汪辜會談”正式舉行,恰巧又是整三年。這是一種時間概念上的巧合!還是這“三”字冥冥之中意味著什么佛家讖語?閩粵臺地區(qū)素以“三”字音同“生”而示吉祥,這兩個“三”字是否意味著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之意呢?從最近報章發(fā)表的追憶汪老的有關文章中了解到,中央早在1988年就有意請南懷瑾先生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隱士式的人物作為兩岸關系的傳話人。而在張尚德先生回到臺灣后發(fā)表在達摩出版社當年12月出版的回憶文章中提到,進入大陸前夕,他們特意拜望寓居香港的南懷瑾先生,“上師(筆者注:張尚德先生對南懷瑾先生的尊稱)訂了豐富的大餐招待大家,北平(筆者注:指北京)來了‘客人’……,好是‘情懷’!”北京來了什么“客人”?為什么在這后面用了省略號?“好是‘情懷一又指的是什么?對此我不能妄加猜測。但從后來媒體中披露的只字片言中隱約可知,當時南先生在香港的寓所中兩岸密使已有了接觸……
我想,汪道涵先生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作出與張尚德先生會面的舉動,很可能是緊急征求了中央最高領導的同意,也可看出汪老在當時已經產生了籌劃兩岸關系接觸的念頭或已經開始進行兩岸關系的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