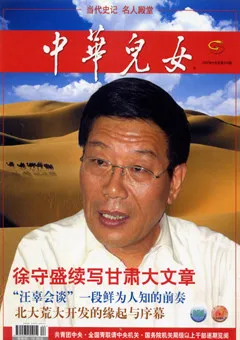話劇民族化的先行者焦菊隱

現(xiàn)在和年輕人提起焦菊隱來,大約知道的人已經(jīng)很少了。然而,提起北京人藝的話劇《茶館》、《蔡文姬》,很多觀眾切是有著很深的印象。其實(shí),這兩個經(jīng)典作品就是焦先生導(dǎo)演的。作為以為戲劇大師,一位中國話劇民族化的先行者,他的功績理應(yīng)給載入中國藝術(shù)和中國話劇史史冊。值此中國話劇運(yùn)動100周年之際,讓我們再次走近這位民族化的戲劇大師——
北京人藝的總導(dǎo)演
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經(jīng)歷了半個世紀(jì)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在排演出一人批經(jīng)得起歷史和觀眾考驗(yàn)的優(yōu)秀劇目,造就出眾多杰出的導(dǎo)演藝術(shù)家和表演藝術(shù)家,磨礪出以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民族化為創(chuàng)作方法的“北京人藝演劇學(xué)派”,特別是在中國話劇整整百年的今天,面對這一切,最讓劇院同仁們和廣大觀眾深深懷念的,就是人藝第一副院長、總導(dǎo)演焦菊隱先生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guān)懷下,焦菊隱與曹禺、歐陽山尊、趙起揚(yáng)一起創(chuàng)辦了北京人藝。焦菊隱“為了創(chuàng)造具有民族風(fēng)格、民族氣派的中國話劇”,嘔心瀝血竭盡全力,先后導(dǎo)演了《龍須溝》、《明朗的天》、《虎符》、《智取威虎山》、《三塊錢國幣》、《茶館》、《蔡文姬》、《膽劍篇》、《武則天》、《關(guān)漢卿》等一系列經(jīng)典名劇。
他不斷思索與實(shí)踐,專心致意地琢磨構(gòu)思,沉迷于他所理想的戲劇境界。他精心揣摩,著意推敲,不放過任何能說明戲劇核心思想的光色、畫面、音樂與情調(diào),不忽略意義精微的臺詞與動作。他在舞臺上縱橫揮灑,創(chuàng)造出既符合作家的意圖又豐富作家想象的意境。他的導(dǎo)演工作,精致確切。常常是經(jīng)過無數(shù)晝夜,終于得心應(yīng)手,立下“意”根,畫出枝葉,放出一片明麗的朝花。
他為北京人藝開拓新的藝術(shù)境界。北京人藝的演員們在他想象聯(lián)翩的導(dǎo)演過程中,得到耐人尋味、生動的啟發(fā)。有時,如急風(fēng)驟雨,掀動起排演場上的創(chuàng)作激流,有時,在寂靜如空的沉默中,冒出三兩句精到入微的妥貼言語,挑動起演員的創(chuàng)造心情。他的話如春雨落花,自自然然飄落在演員的領(lǐng)悟中。
他隨時啟發(fā)演員對角色的真實(shí)感請,校正演員的創(chuàng)作路標(biāo),引導(dǎo)演員對人物廣泛深刻的探尋。演員從毫無收獲的苦惱到偶有所得的歡快,兩種心情反復(fù)交替的過程中,最后摸著了角色的真諦。焦菊隱才肯定這個角色性格的基調(diào)。
他在北京人藝盡心致力于中國話劇民族化的創(chuàng)造,奠定了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的基礎(chǔ)。他創(chuàng)造了賦有詩情畫意、洋溢著中國民族情調(diào)的話劇。他是北京人藝風(fēng)格的探索者,也是創(chuàng)造者。
樹有根,水有源
焦菊隱原名焦承志,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紹興。他自幼家庭貧寒,但是從小學(xué)到高中一直學(xué)習(xí)勤奮,成績優(yōu)良,后來被學(xué)校保送考入北平燕京大學(xué)。那時,他便開始寫作、翻譯、兼做家庭教師,以支付自己上學(xué)所需的費(fèi)用。

焦菊隱1928年在燕京大學(xué)畢業(yè)以后,于1931年,受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的委托,籌辦“北平戲曲專科學(xué)校”(后改為“中華戲曲專科學(xué)校”)。焦菊隱任校長;李石曾任董事長。作為一個“洋學(xué)生”辦戲曲學(xué)校,當(dāng)時是首創(chuàng)。焦菊隱一方面繼承科班教學(xu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注重學(xué)生的基本功訓(xùn)練;一方面重金聘請各個流派的藝術(shù)家傳授表演的經(jīng)驗(yàn)。他采用一整套全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學(xué)方法,施行男女合校,并開創(chuàng)京劇音樂伴奏專科課程。學(xué)校的學(xué)制為8年,學(xué)科包括有國文、歷史、音樂、話劇、習(xí)字、工藝、國畫、昆曲、做工、唱工、武工、武術(shù)、軍訓(xùn),還有外文,等等課程。在學(xué)生個人考核欄里,有禮貌、語言、習(xí)慣、衛(wèi)生等情況的考核。同時,他提倡破除后臺供奉、禮拜“祖師爺”的舊習(xí),并免去演出時的飲場、扔墊子等陳規(guī)。演出時,演員名次排列一律以出場先后為序。排練時,他要求突出人物性格,對一些傳統(tǒng)唱腔也作了革新。
戲校開創(chuàng)時培養(yǎng)的“德、和、金、玉”班學(xué)生中,有不少人曾經(jīng)先后成為活躍在戲曲舞臺上的優(yōu)秀演員和優(yōu)秀教員。例如,傅德珠、宋德珠、王和霖、王金璐、李金泉、侯玉蘭、陳永玲、高玉倩,等等。而且,在此期間焦先生曾經(jīng)拜名優(yōu)曹心泉、馮惠麟為師,學(xué)習(xí)小生戲;向鮑吉祥先生學(xué)習(xí)老生戲;還向王瑤卿、陳墨香兩位大師求教戲曲藝術(shù)。
北京解放前夕,焦菊隱又把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改編為京劇《鑄情記》,并親自作導(dǎo)演,主要演員是王金璐和高玉倩。這是在中國戲曲史上,第一次把莎翁的劇本搬上京劇舞臺。
然而,戲校的改革遇到金融界的政客們的阻力和壓力,最后,焦菊隱被迫辭職。1935年,他離開了中華戲曲專科學(xué)校。李石曾為了安撫他,拿出一些費(fèi)用,送他去法國留學(xué)。
焦菊隱考入巴黎大學(xué)做一名研究生,攻讀文科博士學(xué)位。當(dāng)時,焦菊隱只學(xué)過英文和德文,已經(jīng)是30多歲的他,再另外在短期內(nèi)學(xué)習(xí)法文和拉丁文是很困難的事。同時,巴黎的生活費(fèi)用很高,焦菊隱在得到導(dǎo)師允許的情況下,又到物價比較低的比利時去學(xué)習(xí)法文和拉丁文。
那時,焦菊隱為了節(jié)省不買東西,也很少參加社交活動。他非常珍惜時間,每天不完成學(xué)習(xí)計劃就決不休息。他熱衷地吸取各種知識,學(xué)習(xí)和觀摩了西方古典和現(xiàn)代的許多文學(xué)、戲劇作品及演出。同時,還有系統(tǒng)地整理他過去所研究的中國傳統(tǒng)戲曲方面的知識。
后來,焦菊隱以流暢的法文撰寫了博士論文《今日之中國戲劇》,還有兩篇導(dǎo)師指定的副論文——《唐宋金元的大曲》、《亨利·貝克戲劇中的社會問題》。
1938年1月,焦菊隱被授予巴黎大學(xué)文學(xué)博士的學(xué)位。他的論文《今日之中國戲劇》,由巴黎德羅茲出版社刊為“世界戲劇叢書”出版。
1938年上半年,焦菊隱毅然回國投入抗日戰(zhàn)爭的洪流。他就任江安國立劇專的話劇科主任,教授導(dǎo)演、表演、舞臺美術(shù)和劇本宣讀等課程。同時,他在大后方和北平先后導(dǎo)演了話劇《一年間》、《明末遺恨》、《日出》、《原野》、《桃花扇》,以及《夜店》、《上海屋檐下》。
歷史證明,焦菊隱是一位學(xué)貫中西、通曉古今的戲劇大師,而且也是一位飽經(jīng)滄桑的愛國者,這些為他后來立志不渝地促使中國話劇民族化,打下了堅實(shí)而可靠的基礎(chǔ)。
“欣賞者與創(chuàng)造者共同創(chuàng)造”
眾所周知,作為藝術(shù)門類之話劇是一個西方的舶來品,從1907年6月華人留學(xué)生組織的劇團(tuán)“春柳社”,在日本公演《黑奴吁天錄》(即由美國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改編而成)以來,中國正式出現(xiàn)了一種西方戲劇的演出形式——舞臺上呈現(xiàn)為分幕的結(jié)構(gòu),用對話和動作來演繹故事,塑造接近生活的各種人物形象。1928年經(jīng)話劇的奠基人、戲劇家洪深提議,把這種演出形式定名為“話劇”。因此,也可以說自中國話劇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一個如何民族化的課題。或者說,中國話劇一直面臨著一個如何締造具有中國作風(fēng)、中國氣派、中國感情的民族話劇的課題。
焦菊隱幾十年以來,正是從理論和實(shí)踐的結(jié)合上,潛心執(zhí)意于解決中國話劇民族化的課題,而且成就卓著為世人所知,并已經(jīng)做出了突出的貢獻(xiàn),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里,僅從一個核心點(diǎn)上,作一些簡略介紹。
焦菊隱多次提出了自己的審美主張,即戲劇觀:“欣賞者與創(chuàng)造者共同創(chuàng)造。”很明顯,這正是中國民族戲曲的基本特征。沒有觀眾的參與,沒有觀眾與演員的共同創(chuàng)造,戲劇演出就無法完成,這是個總開關(guān)。這里,如何對待和認(rèn)識觀眾是話劇民族化的出發(fā)點(diǎn)和歸宿點(diǎn),也是其根本之所在。所謂“共同創(chuàng)造”就是充分調(diào)動出觀眾的想象空間,調(diào)動得越多、越大、越深就越是成功。我們應(yīng)當(dāng)做到“不直,不露,給觀眾留有想象、創(chuàng)造的余地。”這種例子在豐富多彩的戲曲里比比皆是,如——一根馬鞭就是一匹日行八百的好黃驃馬;臺上跑一個圓場就是越過了萬水千山;一句“后堂吃酒”就是一頓招待客人的盛宴,等等。由于焦菊隱的探索和實(shí)現(xiàn),在話劇《茶館》和《蔡文姬》中這種“舉一反三”的例子也并不少見。在“共同創(chuàng)造”的理念之下,焦菊隱還談到了一些具體方法,比如:“通過形似達(dá)到神似,主要在神似。通過形使觀眾得到神的感受。關(guān)鍵不在形,但又必須通過形。”在《茶館》第二幕的開場里,王利發(fā)準(zhǔn)備茶館的重新開張,正在把“莫談國事”的標(biāo)語,一張張粘貼在了墻上,粘貼得多了,雙手就難免要粘上一些漿糊,為了不讓漿糊蹭在衣服上,于是兩只手只好扎挲著,連挪桌子上的針線笸籮也要用胳臂肘捅開。這里,通過“形”使觀眾得到“神”的感受,也就是讓觀眾充分地展開自己的想象——既想到了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箭穿雁口,沒有任何言論自由;又想到了王掌柜一生膽小怕事,要“當(dāng)順民”的思想性格。實(shí)在是妙不可言!
這些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張的舞臺就是“四堵墻”的戲劇觀是很不相同的。一個是主張演員和觀眾在同一個空間里,進(jìn)行共同的創(chuàng)造;一個是要把演員封閉在“四堵墻”里,當(dāng)眾孤獨(dú)地與觀眾隔離。
事實(shí)證明,只有推倒“四堵墻”,才能實(shí)現(xiàn)“欣賞者與創(chuàng)造者共同創(chuàng)造”,也只有實(shí)現(xiàn)“欣賞者與創(chuàng)造者共同創(chuàng)造”才能使話劇真正的做到民族化。正如焦菊隱所總結(jié)的:在戲劇發(fā)展當(dāng)中,有三個要素是不能分開的。“作者、演員和觀眾。我們殷切地希望他們能夠懂得他們之間的互相合作是一件多么緊迫、多么重要的事,因?yàn)橹挥凶龅竭@一步,中國的戲劇才能成為人類的一種珍貴的精神食糧